
作者(第三排最左)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中文课上。
COURTESY OF JESSICA MAY LIN 林嘉燕
我大学第一堂中文课,老师问了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问题:“告诉我,华裔在美国受歧视吗?”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上一个专门给华裔设计的班,学生都是ABC(即美国出生的华人)。我们八点钟来上课,还在半梦半醒状态中。有的学生在啃面包,有的趴在课桌上,但我们差不多都摇头表示否认。
老师笑了。“嗯,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学到美国是个平等的地方。当你是一位学生,这可能是真的,但一到你毕业了,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你还是受歧视。所以你必须学中文,以便人家欺负你的时候还有另一半身份可以给你自我把握。你这样才有一个完整的身份。”
这位来自大陆的老师敢第一天说这么严肃的话,我们都吃惊了。当时我才上大二,感觉老师解释的情况离我很遥远——不过从一开始我就对我的中文班格外注意,一部分是因为我中文老师的观点跟其他老师确实不一样,一部分是因为学中文曾经是我最恨的活动。
同学们分帮结派
回到我的童年。跟中文的关系一直是我生活中最复杂的关系,因为它反映了我跟父母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我对中国的认同感,随着我的成长经历也一直在变。我的父母1983年从北京移民到加州湾区, 1993年我在加州出生,后来祖父母也从北京移民到美国帮助照顾我。小时候,我们在家说的语言是中文。我正式学了八年中文,也可以说我非正式地在家里学了二十几年的中文,但在每一个时段,我的情绪都不一样。
我上的第一个中文学校是一位台湾老师办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下课以后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学、三位男同学会站在路边,等着一位师傅开面包车接我们去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厨房里总是准备了一大锅卤肉饭。吃完饭,老师每天会带我们读一篇新课文,然后辅导我们练习写字。如果学生很快把字练好了,老师也会给我们数学题做;聪明的同学都会假装做不完, 然后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在桌下玩儿掌上游戏机。
我们中文学校的学生都是华裔孩子,家里情况差不多——父母要上班,所以下课以后没地方去。很多同学会参加小学的课后项目,但我妈看到这些孩子下课在外面玩儿,还吃糖果和方便面,觉得浪费时间又不健康,在中文学校至少能学一点东西。
在那段时间,中文学校不只是我放学以后混时间的地方,它也是我们的小社交圈。不同小学来的孩子会各自形成小团体,抢其他小学孩子的书包。我们也会按着父母的来源分帮结派,因为中文学校一半的同学父母是从台湾移民来的,一半是从大陆来的。在一起玩儿的时候,连小孩子也经常会争吵海峡两岸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一位叫贾森(Jason)的同学对这个话题尤其激动,后来上中学的时候不只是华裔同学,其他种族的同学也喜欢逗他说“贾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爱激动,觉得好玩儿——但实际上我们也不懂,只是在模仿父母在饭桌上的话。
在我所住的旧金山湾区,普通话的中文学校实际上不少,但父母还是选择送我到这家台湾老师办的学校,是因为湾区大多数的中文学校一周只开一次课,不像我当时的中文学校每天下午都有课有活动。令我父母觉得有意思的是,自己是大陆人,但孩子学的却是繁体字。他们经常让我朗诵注音符号,觉得好玩儿。
虽然学了跟父母不同的写字系统,但中文学校对我的中文有很大的帮助。华裔孩子第一个语言通常是中文,因为是父母交流的语言,但一旦孩子开始接触学校里说的英文,跟朋友和老师都用英语交流,就会把英语当成主要语言,不再跟父母说中文了。在我认识的华裔中,很多父母也会用英语回答孩子。久而久之,很多华裔孩子的中文水平就会退步,有的孩子会完全忘记中文。我大多数的华裔朋友只会说几句中文;在我家春节和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我的堂亲听不懂大人在饭桌上说的话。我自己九岁才开始只用英语跟父母交流,比其他孩子晚了几年,正是由于课后中文学校的影响。
广告
当时在家里,我爸也会用英语回答我,但我妈一直坚持用中文跟我交流,甚至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会很奇怪——两人说两种不同的语言,即使就这样还是帮我保持了我的听力和口语能力。小学时候,我还开始喜欢偷看我妈看的武侠电视剧,因为我喜欢那些大侠穿的衣服,比如女英雄轻飘的袖子。当时我妈可能以为看电视剧耽误学习,但我认为这些电视剧实际上保持住了我的中文。
更重要的是我们住在一个华人多的社区。生活在湾区,即使我不主动锻炼我的中文,也有机会学。在超市里排队交钱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旁听周围夫妻的谈话,在公园玩儿的时候也会听到喂鸭子面包的爷爷和奶奶在讲中文。我放寒暑假都是姥姥和姥爷照顾我,他们英文不流利,所以我只能跟他们用中文交流。我八岁时候,爸爸回国搬到成都创业,从此以后我和妈妈每年夏天会探亲一个月。在这些旅行中,我还是坚持只跟父母说英文,但在街上买冰棍和盐酥鸡就必须用上中文,跟隔壁住的孩子玩儿也都是说中文。我后来才发现这些看似随意的经验训练了我理解不同方言和口音的能力。
我的梦魇
再大一点(差不多九岁时候),我开始参加课外活动,放学后要拉小提琴、弹钢琴,还要去拉拉队训练,就没时间每天学中文了。当时我父母跟许多华裔父母一样,让孩子从九岁或十岁开始参加对申请大学有利的课外活动,争取让孩子变得多才多艺。在这个逻辑下,华裔孩子会说中文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父母会把时间和关注放在别的活动上,最流行的是钢琴等乐器。我开始忙碌起来,只好换到周末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天上两小时课。
除了几位我们当时羡慕又讨厌的学霸,周末中文学校是每一位华裔初中生的恐惧:要牺牲我们的周日坐在教室里,同时想到其他朋友正在家里一起玩儿,感觉非常难过 (有几次我妈忘记了夏令时改成了标准时间,等我们开车到了中文学校,发现已经错过了一半的课,我记得自己兴奋死了)。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教课并不差,但是中文学校失去了之前的亲密。小时候我的社交圈围着中文学校转,而到那个年龄我的朋友是通过少年乐队与其他活动认识的,中文学校好像是那些书呆子周末没事干去的地方。
更关键的是,我当时认为学中文没有意义。那会儿我有着典型的十来岁女孩的叛逆倾向,心想:毕竟我父母这么努力移民来到美国,想要我在美国成功,为什么又要让我倒退学中文呢?过节的时候,许多来我们家的阿姨看到我不主动说中文,以为我不会,就对我妈说,“哎呀,你的孩子不会说中文,多可惜啊!” 听到这种话我就会翻白眼,等她走了之后对妈妈埋怨,“为什么中国老太太总是觉得孩子必须会说中文?中文对我的日常生活没有用,我也不会有一天搬到中国住……为什么要学?”
在这段时间我参加了两个不同的中文学校,都是两位很有经验的大陆老师开的。第一个在附近的高中,课程很轻松,大多数的孩子是来混时间的。第二个是湾区最认真的中文学校,一共分十个年级,我当时小学六年级进了七年级中文班,班上同学有初中学生、高中生,还有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学霸,正在读《西游记》,每周上课都会带着小说来给老师看,老师也读她写的文章给大家听。
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其他学生的妈妈,业余时间教中文。为了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每半年学生升一级的时候,老师保持不变。我一直很怕我的老师,因为她教课很严,有几次我没有准备课文,她看出来了,让我在全班面前朗诵唐诗,害得我在暗恋的男生面前非常不好意思。虽然很痛苦,我确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七年级背唐诗,八年级开始学成语和《论语》,九年级是写作班,十年级学毛笔字。这些项目其他中文学校都没有,老师也反复强调我们有这个机会很幸福。
学校还有一位白人男生,我们都觉得他很奇怪——毕竟那是2006年,在美国初等学校学习中文还不普遍,周末中文学校是一个华裔孩子传承文化的工具,为什么一位不是华裔的孩子会来学中文?我们开玩笑地问他父母是不是疯了才把他这样一个白人孩子送到这样的“监狱”里。几年后我在一个网站上读到一个那段时间留下来的评语,我猜是这位孩子的妈妈写的。她最大的批评是我们的课程强调死记硬背,不是美国的“growth-oriented”(增长型)授课方法, 而且课程假定孩子有很强的中国文化背景,其他背景的孩子很难理解课文,加上她自己不会中文,就辅导不了孩子做功课。
我妈一直在强调“有一天你会感谢我”,老师也一直强调“中国文化是你们的一部分,必须好好学”。但在年幼的我看来,生活在美国,我的中国背景对我弊大于利。有一天下中文课后坐在车里,我把书扔在地上,对妈妈说,“我不学了。”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但这一次不一样。这次说完后,我再也不肯翻开中文课本了。我妈怎么劝我,都假装听不见。她没办法,就只好放弃了。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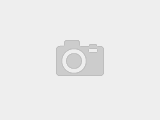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