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食物,品味的争辩可能很激烈,甚至离谱。荤食者杠上素食者,吃在地食物的人(locavore)杠上超市主顾,甚至,喜欢吃真空包装、煮出来白扑扑黏糊糊的肉品的人,杠上成天与铸铁锅为伍的人。可是说到在乎品味的人最在乎的那种品味,争辩不仅更直接,而且更特殊。因为我们所说的「品味」,指的是小品味──我们送入口的东西的滋味,也指大品味──我们装饰自家墙面、穿衣打扮和过生活的方式。这里有唇舌品味,也就是你吃进东西时的感觉──它是咸的、甜的还是苦的或香浓或介于之间,以及带出「酸」这一大类的莱姆和柠檬和醋所呈现的总总细腻变化。此外,还有我们所谓的「道德品味」──在某个时代风格里,或某种自我形象里,我们吃的食物所具有的地位。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两者称为「风味」和「风尚」,而且这样说应该不离谱。只是「风味」和「风尚」显现不出我们对饮食品味的认同深度。在宗教性事物里,我们常看到这种认同的深度。正统派犹太教徒喜欢在逾越节家宴上吃烤胸肉(brisket),但是他们喜吃烤胸肉不仅仅只是风尚。那是一种道德品味──在他们眼里,吃烤胸肉是伦理上的表态。也是从表面上看来较微小的情感面表态。我喜欢丹.巴勃的食物带给我的唇舌品味,可是我喜欢在他位于石谷仓(Stone Barns)有机农场的餐厅吃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风尚。这是一种道德品味,因为被人看见我上那里去会让我感到自豪,而且我也喜欢假装参与永续农产品和老品种计划。
当然,这类「道德品味」,在我们这年代已经被高度道德化:上巴勃的餐厅吃饭,让我们以为自己正在为拯救地球尽一份心力。然而不论在哪个时代,唇舌品味都通向道德品味──两者是相关连的,而且正是这些关连性驱动我们的饮食。我爸妈都只是大学教授,但他们年轻时每年去巴黎,而且在新料理(nouvelle cuisine)的新殿堂吃饭,在盖哈的餐厅或杜图尼耶(Alain Dutournier)的旧餐厅「加斯科尼的窝」(Au Trou Gascon)。在那年代,吃食还没变得这么强烈「道德化」,所以羔羊产自哪里,或是鸭要受尽多少折磨才有肥肝,这些问题都还很次要。我想当时恐怕也没有人会问起这类问题。然而选择法国和法国料理,涉及诸多其他的自我定位。它是一种道德品味,就像从费雪到李伯龄的每个美国美食家一样。它意谓着把饮食升格为一种人文活动,从而意谓着选择巴黎而不是普鲁士,选择欢愉而不是禁欲,选择物质主义的奢华享受而不是中产阶级的缩衣节食,放纵口腹之欲而不是压抑食欲。这也跟性、旅行、上帝、生活……等等的态度有关,从这些方面来说,喜欢杜图尼耶的白豆什锦锅(cassoulet)料理的唇舌品味,以那砂锅何等赏心悦目──又满是白豆──来看,也是道德品味的一环。
或者,看看葛瑞格.克雷邦在时代-生活书系的《经典法国料理》里那六○年代中期动人的一刻,他谈到了他到纽约玛玛戎内克(Mamaroneck)拜访几个对高档料理怀有无比热忱的年轻朋友:「如果他们有汉堡的话,他们也会端出燄烧干邑白兰地胡椒汉堡。如果他们有小牛肉,也会佐上最细致的香草。」他们做教皇清汤(consommé Celestine)和玛古希比目鱼,甜点则是罗斯柴尔德舒芙蕾,然后有人点了一根高卢牌(Gauloise)法国烟,克雷邦写道:「有那么好一会儿,我彷若置身于法国南部。」这不免让我们感到矫情造作,可是在加工奶酪和人造皮革鞋充斥的年代选择幻想中的哈法生活,是一个困难的选择,真心的选择,一个好的选择,在今天则是过于轻易的一种怀旧选择。道德的选择只有在他人把它变得对我们有益的情况下,才会显得愚蠢。

我们有唇舌品味和道德品味──如同鲔鱼查理老早便发现到的,虽然两者关系错综复杂但大不相同。「查理,星琪要的不是品味好的鲔鱼,星琪要的是滋味好的鲔鱼。」在六○年代中期,一系列电视广告里一只聪明的小鱼,曾经跟这只卡通大鲔鱼这么说明,而这尾卡通鲔鱼藉着戴贝雷帽、在家中墙上挂着抽象画等等,试图让星琪公司相信──根据卡通动物想要被人宰杀并吃掉的诡异习俗──牠有着好品味。「品味好的人总会去无人知晓的地方游历。」

关于唇舌品味,我们懂得很多,多半是它有多么容易形成效果。物品的等级,产地的资料──酒标上写着「加州」产的红酒,永远比写着达柯塔州产的来得好喝──它被食用的脉络,在什么之后,在什么之前……这些在在会改变我们的知觉。这些效果当中的一些──吃了朝鲜蓟之后,水喝起来会是甜的──纯粹是生理性的,而且大家都明白。其他的象是酒标如何影响我们品酒,则比较属于狡诈的社会面。但是它们都会形成效果,也就是我们从舌尖上感受到的,比不上我们脑袋里相信的。
譬如说,我们现在知道,除了嘴巴里有味蕾之外,还有更多的另一种味蕾存在于内脏里,它们也机灵地在调整和控管我们的欲望,确保我们吃的不仅是唇舌喜欢的,也是肝脏所需要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多么倚靠某种百试不爽的把戏,或者说,我们胆敢和大脑及其化学反应过招:譬如,我们吃辣椒,只因为我们知道大脑会过度制造麻醉物来抵销舌头的灼烧感。假使大脑不这么做的话,那么辣椒或咖哩其实是让人难以招架的。全世界的文明每晚都在用假动作唬过它们的神经系统。我们学会用感官来感知腐坏,以便享受被精密控制的腐坏滋味,就像从奶酪和松露和马第宏红酒所尝到的。我们不是味觉的吃角子老虎,被动接收味蕾所登录的讯息,我们是扑克牌手,唬咙我们的神经。
可是鲔鱼查理往往也没错。好品味向来是从吃好东西开始。道德品味往往是从唇舌品味延伸出去的隐喻。如果说我们喜欢用来形容抽象智力的隐喻是视觉性的──我们的孩子头脑灵光或昏昧(呃,我们的孩子可不会),我们对未来的愿景一片光明或一片黯淡,我们的问题十足被阐明或模糊不清──那么我们最喜欢用来形容直觉经验的隐喻,都是味觉性的。我们在形容一个人说话的口气时,用的是立即的味觉震撼:那男生或女生说话很甜或很苦,很甜腻或很酸溜溜。

奇怪的是,随着唇舌品味改变,道德品味也跟着变,跟上了革命法则同样的周期循环。哪怕是──尤其是──稳定繁荣的中产阶级,食物的品味和用餐的品味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书之一是《法国料理的经典》,一本收录了法国每个三星殿堂食谱的书:封面有个身穿白厨袍的三星主厨,高傲地打着手势,比向书里所涵盖的经典菜肴──现在看起来象是十二道面目难辨、褐泥似的焗烤料理──书里来自每个伟大法国厨师的食谱,看起来简直不可能做得出来,更别说不好消化了。规则就是这样。二十五年前的好食物,看起来总是有碍健康;五十年前的好食物,看起来总是引不起食欲;一百年前的好食物,看起来总是难以下咽。知识在进步,但烹饪并没有,或者说,只有部分在进步。饮食始终是个仪式,用以确认它本身的存在就是理由。
拉长距离来看,唇舌品位和道德品位的循环更明显了。我们知道一个世纪之前,喜爱非当令食物和异国食物的品味,界定了何谓世故老练的吃食者;可以在十二月吃到草莓和在纽约麦迪逊大道吃到布列斯鸡才是有品味的人。现在,同样开明的用餐者,反倒是以拒绝远地来的和过季的食物来界定;他不会在十二月吃草莓,而且希望他吃的鸡是在他家地下室养大并宰杀的。饮食时时在改变,顶尖饮食改变得和顶尖厨师一样频繁。
想想当令食物在外食这件事的地位。在巴尔札克的《幻灭》里,主人翁吕希安进巴黎的头一晚,在皇家宫殿挥霍了一顿,此后开始在左岸小酒馆吃饭。弗利科托(Flicoteaux)小馆,可怜的吕希安不得不消费的食堂,只提供在地和当令农产。巴尔札克详细描述店主人弗利科托如何只买刚从农场来的产品以压低价格,只在甘蓝的产季买甘蓝,只在芜菁的产季买芜菁等等──也同样详细描述在巴黎城中的食客必须吃得像乡下人所感受到的羞辱和不堪。必须在那里吃饭,是身为诗人的悲哀宿命。贫穷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吃当令饮食。没错,现在我们花三百美元在亚伦.帕萨(Alain Passard)的餐厅吃套餐,在几条街外就吃得到一盘西红柿片──虽说只在西红柿季才吃得到。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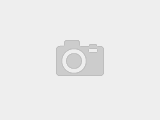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