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婆婆晚餐回来,方敢敞开车窗,才有忽悠悠的风,凉丝丝地在车里游。
满月哦,先生偏偏头向后坐的婆婆说,东方人对满月的感情很特别,安娜一见满月就长呼短叹,从不厌倦。
婆婆指指前面:湖畔公园住着一个无家可归的中国女人,月亮圆的时候还会载歌载舞呢。
我惊奇,这个小城鲜见无家可归的人。那个湖小得有些说不过去的公园么?前次来探访婆婆,我还和先生午间去过。一汪边角都不齐整的水池,不圆不方,那形状仿佛是蜡烛的一焰火芯被拦腰吹了口气儿,再不然就好像营养不良的月牙儿。真有人把它当湖么?怎么确定是中国女人?这城里华人少得可怜呢。
这里的居民都知道这个中国女人,我们教会的人接近她,想给她些帮助。她自己说从中国一个有着特别大的湖特别圆的月亮的特别美的地方来的。她英文还算流利,除了些食物之外,拒绝我们其他的帮助。
她没家?
她说以前有家,家里有很好的丈夫,后来美国很坏很坏的男人把她骗过来,她就没有家了。
联络不到她的丈夫么?
她不说,每次都重复那几句话,最后总会很小心地说她自己也是个很坏很坏的女人,不能有家。她说“很”的时候会反复强调好几次。
又是个伤心的故事,先生对这方向盘,感慨,男人女人的好和坏说是说不清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清。
婆婆拍我的肩,屏着一半气息:安娜,看那儿!
夏夜的月色下,宽阔的草坪上还浮着墨绿的颜色。湖畔公园的小水潭边,一个纤长的身影梦游般甩动着手臂,扭动着腰臀,《古堡幽灵》那部电影里的镜头登时就想起来了。
先生悄悄把车在一丛茂盛的矮树旁停下来,我怔怔地望着那个自顾忘我地在异乡月下手舞足蹈的中国女人……
婆婆压低声音:她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蛮好看的一张脸,我送给她节日点心的时候,她很有礼貌呢。她白天会在附近出没,有人甚至在城中心看见过她,她的东西都装在一个赢叩超市的购物篮子里,摆放得十分整齐,傍晚大都会到这儿来,估计在这过夜。
守着一潭水住,多危险。我心里的不安跟着空旷的草地上不时冒出的虫鸣,等一声没一声,突地出来,又接将不住,张皇失措地悬在草隙里,没着没落的。

她坚信这湖还在慢慢长大,她等着看它长成满月。
我的手刚刚放在车门把手上,婆婆和先生就同时拉住我:安娜,不安全的。我们帮不到她。
至少我会说华语,也许可以帮点忙,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
安娜,我之前刻意不提,猜到你会心痛。很多人尝试过帮她了,一个跟她说过话的华人说,她疯了。有不少邻里觉得危险,向社区求助,我们在等消息。别在晚上去接近一个疯子。
女人身着一套带着帽兜儿的休闲装,浅的颜色,婆婆说那应该是淡粉色的。看不清她的眉目神情,从她悠荡在草地之上的身影看得出她痴醉在她的世界里。我更听见她喉间咿咿呀呀断断续续的吟唱声。她少女般跳动的时候,两根长长的发辫绕着她的肩背上下翻动,如一双亢奋的蛇影。
心里横七竖八的都是酸涩,眼泪似乎说盈则溢。先生仍旧拉着我的手:安娜,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我知道不少中国女人利用和美国公民结婚取得美国绿卡,一拿到公民身份就把美国丈夫踢开。也有不少美国男人利用婚姻把中国女人骗过来,结局耸人听闻……你说过的,孤掌难鸣。
别说了,回家吧。婆婆催促,不早了。

从婆婆家归来,旧金山湾区的家,楼下临着的是名副其实的湖,站在楼上晒台望下去,才诧异:住了几年,才看清这湖的形状,硕大的一个腰果仁儿嵌在安稳的一群小楼之间。忍不住想起那个月下起舞的女人,她在中国有着怎样的故事?她来美国又陷入了什么遭遇?究竟是多么深的伤多么彻底的痛多么沉重的愧疚让她选择流浪,让她选择永远走进痴滞癫狂?
入了秋,晚间就遇着了秋寒,婆婆来电话。寒暄几句,问她:那个中国女人怎么样了?
哦,她不见了。上个月人们才觉察,也有人四处找了,仍旧不见。现在孩子们还记得那个湖畔的中国女人,因为他们仍旧被警告傍晚不要去那里走动……
没有相关的新闻吗?我蓦地打了个激灵,秋天真的来了。
没有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安娜,别再想这事,对你没有好处,想些高兴的事……
异乡的那个湖畔,月亮再次圆至中天的时候,再看不到那打着长辫子的中国女人且歌且舞了!一根草枯折了,来年随春而归,人呢?跟日子一样,走了,就没有了,尤其在遥远的异域,烟消云散,不留痕迹。听人说过:有家的人是泉水,无家的人是雨水。雨水无根,薄喜浓愁。
唉,这个随即而来的中秋夜,那湖畔公园,只一轮满月,半潭秋水。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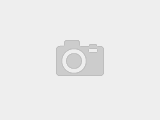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