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批评一直是比较刻薄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是犀利。这是朋友给我下的定义,我觉得也对。因此,我和作家的关系,自然也比较复杂。有些作家,比如陈忠实、杨显惠,作为前辈,他们都很善意地接纳了我的批评,并成为了忘年交。有些,就似乎成了仇敌,老死不相往来。还有一些,就在不离不弃之间,场面上都可以应付一下,但肯定没有私交。李建军说,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几个仇敌作家,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似乎也有道理。本来我生性淡薄,不善交际,正好可以静心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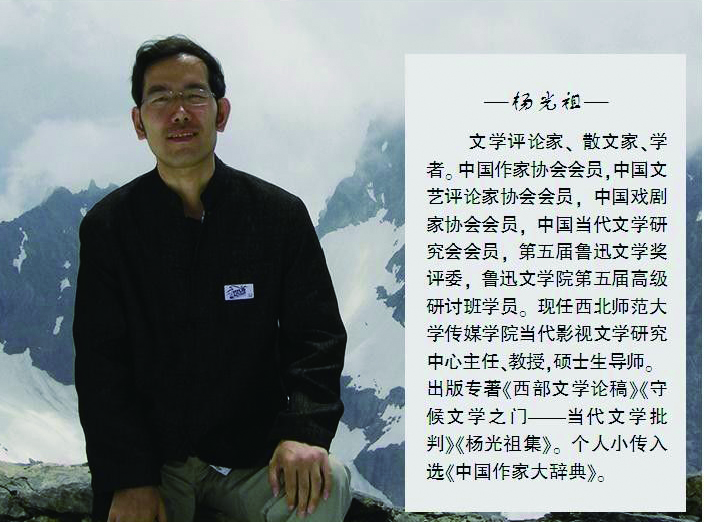
多年前,在兰州一个晚餐上,与几位朋友吃饭、聊天,不知怎么的,谈起了文学批评。有一位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的哲学教授看着我说:“当你持刀将对手砍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的衣服上也溅满了鲜血。”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反思我的部分文章了。
我一直是鲁迅的信徒,他的寸铁杀人,是我钦佩的。他的杂文,也是我极其喜欢的,从初中就开始喜欢。唐代诗人贾岛《剑客》一诗,我经常吟咏:“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似乎自己也一直在磨一把剑,觉得自己是一位剑客,孤独剑客,独走江湖。我觉得像小李飞刀那样,真正的一剑封喉,那才是最高境界。砍得大家遍体鳞伤,那是多么可怜复可悲。因为文学批评毕竟也是一门高雅的行当。
所以,我后期的文学批评措辞含蓄多了,不那么放言无忌了。朋友说,我温和了,其实,也可能与年岁有关系,毕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但是,有一点我却一直坚持,就是我尊重,我批评。我曾在《南方文坛》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是一种致敬》。读者细看我的文章,凡是我批评的作家基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可能是爱之深、求之切吧。这点我与别人有所不同。至于那些我瞧不上眼的作家作品,我几乎都不会说话,如果必须说,也一定不说名字。但作家却不体我之苦心,只要一看你在批评,就翻脸不认人。我得罪的作家少说也有一打了,李建军安慰我说,得罪作家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不过,也有一些作家在看到我的尖锐批评后,并不为意,而是正常来往,甚至对我青眼有加。这以前辈作家为多,比如陈忠实、杨显惠。我与杨显惠老师每次相见,都吵个不亦乐乎,但所吵都是因为文学,吵完了,大家拍拍手,散了,下次聚会,还是吵。有时,我想,我何德何能,有资格与杨显惠老师过招?但下次见面,还是吵,当然,也有平心静气深度交谈的时候。杨显惠老师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一位性情中人。


还有一位前辈与我来往十多年,我们之间,有批评,更有深厚的友谊。他对我的批评不但不以为忤,还多方提携我。他的高贵人品,是我佩服的,他可能喜欢的是我这种孩子式的童言无忌吧。他,就是王充闾。我们2003年8月在中国作家三峡行采风团里相识。一路上,他随口就能背诵出很多与所见景物相关的历代诗句,这看来是童子功了,我深为佩服。但我回来,读了他写的《读三峡》《重读三峡》,很不以为然。就全面阅读了他的散文,写了一篇评论《王充闾散文的一种解读》,我在文章中评价说:“王充闾的散文几乎都是杨朔模式的巧妙伪装。……说‘巧妙伪装’,是因为王充闾先生在写作中大量使用古典诗词、历史文献,况且他本人旧学根底不错,经常还写几首古诗词,即便颂歌,也就非常隐蔽了。到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充闾散文最大的特色,或者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古典文史素养带来的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氤氲的古典诗词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他散文灵魂的苍白。如果去掉这层皮,王充闾散文,在精神层面和当年杨朔的散文、贺敬之的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
当时是年少气盛,一吐为快,不计后果。如今看来,话虽然有道理,但后面详细的文本分析似乎有点刻薄了。我一直认为,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它需要的是精神、思想,当然也有学识,这里的“学识”,关键是“学”后的“识”。如果只是堆砌一些古诗词、古文献,那就连“学”也达不到。
这篇文章王充闾先生看到后,没有觉得年轻人怎么背后来一刀,而是很大度地一笑而已。从后来我们俩密切的书信交流中,从他对我的提携中,可以看到他不仅没有生气,相反似乎更喜欢我。他是前辈,他对一个晚辈的调皮,也还是认真对待和理性思考的。这种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真可算是文坛佳话了。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我们看到太多的乱象,要么就是批评家成了作家的跟班,甚至变相的经纪人,要么批评家成了作家的仇人。而作家辱骂批评家最多的一句就是:你有本事写一本看看?在有些作家眼睛里,批评家的文字没有创造性,是不能算作文学的。他们狂妄地认为批评家只是作家的附庸,是靠他们吃饭的,似乎没有他们,批评家就要饿死。更有轻狂之辈,甚至认为批评家无法匹配作家,无论智商,还是情商。听到这话,我都怀疑这样的作家是不是有智商或情商。我们的文坛缺少像王充闾这样的作家——能够与批评家进行平等交流的作家。


其实,某种意义上,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20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批评,普遍有一种趋势,就是力图让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科学。但我一直认为,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科学,而应该依然是文学,是艺术。它和文学创作一样,同样富有创造性。杰弗里·哈特曼说,我们能否把文学世界分为创造性的文学和附属的评论两部分呢?评论就没有自身的创造性或者非附属性吗?这个质问是有力量的。
批评和文学创作,其实是相互独立的,虽然有交叉,但并不是附庸,谁都不是谁的附庸。批评家也不要想当作家的导师,作家也不要认为批评家是你的跟班。大家都是在创作,各在各的领域内。作家读了批评家的文章而有启发,也是常见的事情。批评家读了作家的杰作,也是一种人生享受,得益良深,有感而发;读了作家的劣作,愤而批评,也不是因为个人私怨,而是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批评既是对作品的深度解析和独特阐释,也是提升读者的理解能力、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的手段,更是深入钻探文学的特质,从而将文学不断引入新境界、新领域的必要途径。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撰文《批评家即艺术家》,他说,创作能力与批评能力之间的对立完全是人为的。没有批评能力,就没有艺术创造。他认为:“毫无疑问,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