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写了四十几年小说,在整个写小说的生涯当中,《黄棠一家》这本书算是比较特别的。我个人在小说方面的兴趣基本上比较偏重形而上,对社会生活、对时政、对历史没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的写作原本和人群结合得不够紧密,应该说是比较脱离群众的。前些年我生了大病,生病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一点改变,觉得实在的生活离我的距离近了,因为原来你可以天马行空,你可以个人不管社会、不管其他人,但是生病以后一下打回原形,原来也一天在吃三顿饭,我也得购物,我也得用劳动换钱养家糊口。生病以后突然觉得离人群近了,在生病之后重新再写小说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还债的心情,觉得原来还是欠了一笔债,欠了我和周边人们的债、我和读我小说的那些读者之间,我欠他们一笔债。所以忽然关心起当下、关心起人群,忽然形而下。
这是我打算写形而下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写的是财产、遗产的纠葛,叫《纠缠》,第二部我本来小说的名字叫《荒唐》。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和我儿时的世界比起来特别陌生,觉得什么事情都偏离了原来的样貌,尤其是价值偏离得格外厉害。我是一个老铁路人,我爸爸妈妈也是铁路,我自己最初也是在铁路,我读了铁路的中专,进了铁路的火车头单位机务段,从那考大学离开铁路,我对铁路知道的比较多。在我的概念里,比如说桥,桥和星辰日月一样,我感觉就是永恒的东西。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随便翻中国的新闻,你会发现哪哪的桥又塌了。在我们看来,扶老携幼是一个普遍的人道法则,但是在今天,真有那些老太太、老头倒在路上,大家走到近处发现要绕半圈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从国家层面有一些伟人、有一些大人物,比如像马克思、达尔文、托尔斯泰,有那么一些巨人,但是今天的巨人,每天教导中国人民的是一些商人、有钱人,在首富榜上哪一年排在第一、哪一年排在第二,是这样一些人。
我想说的是,好像这个世界和我儿时的世界,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当了十几年老师,用上海人的话就是,真是两样了。觉得无论什么都有点不对,什么什么都有点不对。所以写《黄棠一家》的时候,觉得特别近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约瑟夫·海勒,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家,都说“文无第一”,我认为小说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差不多可以当他是第一,大家都知道他的《二十二条军规》,我个人特别喜欢,因为那本书翻译、出版都是我深度参与了,叫《上帝知道》,我觉得能写《上帝知道》的人是小说历史上最最了不起的家伙。他有一本书,也有中译本,但译得不太好,译成《出事了》,那本书介绍过来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标题,叫“出了毛病”。我觉得我要写的这个黄棠,其实就是写这种心情、这种情况,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出了毛病。

我曾经想过这本书还应该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故事,是在今天囊括了好多方面的特殊的家庭,有官、有商,还有时尚,还有艺术,还有既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在一个家庭里我把中国当下社会,我身边见到的那些熟人朋友,把他们的故事写到我这本书里。如果真说有一个主旨的话,就是出了毛病。我曾经想过这本书可不可以叫《中国病》呢?因为它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当下的故事。我知道书出来以后,单行本出来以前先有一个缩写本的在杂志发表,然后还有一个全本的在杂志发表,全本发表的时候因为在浙江的一个小杂志,所以今天这么多人没有人读过,是浙江地方的一个杂志叫《江南》。我还是在这两次发表当中收获一点反馈,就说怎么好像是新闻串烧?写的都是这些年在新闻里经常知道的事情。我记得余华先生前几年的一本书《第七天》,那本书出来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甚至专业批评家指《第七天》像是新闻串烧。因为余华省钱,他自己也不买书送人,我也没机会读到,我这个人不舍得买书,尤其是花钱买活人的书,所以那本书我没读到,我知道这本书。我听到说新闻串烧这个反馈的时候,我知道是说我写得不好,看你这个和看报纸有什么差别?拿一个报纸这些事都知道了,我何必看你的小说。
昨天和媒体的几个朋友面对的时候,媒体朋友也问过我类似的话,我说我们写小说的可能和你们不太一样,我们写小说关心的是纵向,我们哪怕就写一个断面,就写一个横剖面,我们还是关心纵向。我可能比较希望今天大家对这个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觉得熟视无睹,觉得每天就生活在书里的人物当中,大家都特别熟悉,今天看着不新鲜、不刺激,不如《捉妖记》,平时见不到,去电影院才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写的事情不用看就知道你上公交车、上商场,每天听大家说的就是这些事。但是我们写小说的人有一点关心纵向,如果你放到历史里边,假如我这本书运气好,30年以后还有人看,或者是300年、3000年以后还有人看,那时候他们看也挺新鲜的,退回30年要是看这本书里的故事,一个很有身份的老太太暴病在街头,一个很恢弘的大桥说塌就塌了,汽车稀里哗啦摔到河滩里,大家觉得今天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提前30年、过后30年,我相信大家看这个事情挺新鲜的,桥也能塌?30年以前有哪个中国人听说桥塌了!
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是辽宁沈阳,沈阳这个城市老百姓特别迷足球,球迷特别多,原来有一个沈阳市人民体育场,18000个座位,沈阳也是足球城,显然远远不够,在前些年建了一个6万人的五里河体育场,一个大的足球场。好像是十年左右时间,突然把五里河体育场炸掉了,我回去问他们为什么炸掉?它不是很新吗?他们说房地产开发商觉得这块地炸掉换个地方重建,把这个地方作为房地产价值更高,我能赚的钱远远比给你重新买一块地建足球场划算。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时代好多事情都荒谬得不得了,居然河也能干,地球上好像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建在河边,但是有一天突然河干了,泰晤士河如果干了我想象不出人们怎么办?塞纳河如果干了巴黎怎么办?中国人有办法,我这个故事里的城市河干了,这个河道正常,河上的桥面800米,河面宽1000米左右,1000米在这个城市有20公里、30公里,干了以后居然变成聚宝之地,全都是机构,里面最多的机构是沙场,因为基建大量用沙,我刚刚从洞庭湖过来,我听说洞庭湖的湖沙卖到31个省市自治区,可能就是没卖到台湾去。做沙场,里边又是废品处理厂,我有一个知青伙伴,是我所在那个城市的破烂王,10亿富豪,收破烂的。他的主要基地就在河滩里,河滩里面又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包括黑道生意。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就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我65岁,也就是说在我走向社会四十几年时间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世界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我现在住得离人群有点远,我在中缅边界的一个大山上,叫南糯山,也是一座茶山,喝普洱茶的人多半都知道这座山,我住得离人群比较远。面对我生于此、长于此,我自己的祖国,我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记得大诗人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大堰河》里面有一个片断,他回到家乡,回到大堰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是大堰河的客人,是他家乡的客人,是他家庭的客人,那种感受和我的感受有一点像,我在我自己的祖国里,我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已经不太认识这个世界。因为我曾经写过西藏,我在80年代初的时候去过西藏,在许多年里我一直写西藏,我就觉得我对西藏充满陌生感,陌生感极大调动我的神经,我特别新鲜。
我去西藏的时候写的西藏,在当时还算是特别热闹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觉得马原写的西藏很奇特,以前没人这样写过。就是因为我对西藏陌生,我对西藏一无所知,我看什么都新鲜,我就把我这个新鲜的感受尽量复原或者再造,我重新造出一个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而言特别新鲜的一个西藏拉萨。现在我写这本书有一点当年的情形,我个人生活一直是远离人群的,我只要下山,我只要回到人群,我就发现什么都特别新鲜,不怕你们笑话,我们山上在一年多以前突然给我们装了网络,装网络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WIFI,在此之前很多年,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说,就是养牲畜的牧民进城、进酒店、进商场第一件事就是大喊大叫有没有WIFI,没有WIFI叫我们怎么活。原来我以为大家说这个话有什么典故,似乎是很幽默的事,但是一年多以前我家里拉了网络,我开始有WIFI,我用上以后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对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对你们来说耳朵都磨出剪子的当下生活的种种荒诞和荒唐,对我来说特别新鲜,所以我对它充满热情地写。结果我发现,人家说你以为你写的主题新鲜,其实这些事不就是,什么叫新闻串烧?这是我从反馈里面听说的,说你做的就是新闻串烧。我挺沮丧。不过我还是挺高兴,如果今天的人不爱看,我就等30年,30年以后这些事重新变得新鲜的时候,那时候人看,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此文为马原在11月18日《黄棠一家》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摘自九路马书院 本版有删减)
马原,男,一九五三年出生于辽宁锦州,现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当过农民、钳工。一九八二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西藏,任记者,编辑。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 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当代知名作家,曾是先锋派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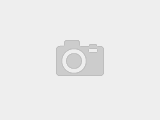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