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的盛春,春寒料峭,冰雪依然的早春更让我动心。正如黎明前的夜最暗,初春的冷有时似乎要比三九天的寒更让人不胜。但有那春的许诺在前面招手,谁还再把身后凌厉北风的威胁放在心上呢?

春的脚步总是那么不紧不慢。从南到北,早春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
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苏南的太湖西岸度过。春天似乎格外青睐这一片土地。记忆里刚过立春,庭院里还积雪一片,奶奶从菜市场就买回新鲜的蔬菜了。那时还没有大棚种植这一说。有两样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叫油菜,但不是开金黄油菜花,菜籽用来产菜油的那种。那厚实且深绿的菜叶子泛着油光。因其含糖分高,即使炒菜喜欢放糖的南方人也在炒油菜时省去了加糖的步骤。另一种则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菜,叫做水芹。这水芹的茎叶柄俱极鲜嫩,无论生拌或炒食都清香爽口。但它的种植说来实为不易。菜农在秋天时将种株植入深土,再在四周深挖沟渠,灌入河水。冬春时节一上市就成为抢手菜。只是不知有多少人在享受这佳肴时会想到鼻尖通红,在刺骨寒风中挖着黏土起菜的农人,和他那双手长满冻疮,在田头水沟洗菜的太太。正如白居易笔下描写的卖炭翁,这位菜农恐怕也是心忧菜贱愿天寒。对于他们来说,春天的诱惑力恐怕无法与对生计的追寻相提并论。

当江南的绿已在枝头显露时,中国北方才从千里冰封,万里雪裹之中苏醒开来。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将近十年。刚开始的几年,我几乎被姗姗来迟的春天急出病来。过了新年,依然是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一晚又一晚的呼啸北风,春天是多么遥不可及。北京市内路旁种植的多是代表古都风貌的国槐。想起来能取代国槐成为北京市树的树种恐怕不多:那样漫长的严冬,那样干冷多风的气候,沙土飞扬,百树凋零,万物萧瑟。在来自蒙古的肆虐北风稍停片刻之际,你可能会在长安街旁的人行道上瞥见一位身裹冬装,时而低头寻觅时而扬首眺望的年轻姑娘。你猜得透她在找寻什么吗?不是丢失的钱包,不是装点华美的新楼。她在努力寻找路旁草坪上任何一点代表春意的绿色,路边的国槐树上任何一点代表生命的迹象。北风吹过,白色的纱巾贴在她红色的脸颊上。多想跺一跺脚,放声喊一喊,把北风吓退,把懒惰的春天从冬眠中唤醒。因为她知道当春天终于来到时,颐和园的十七孔玉带桥会在随风起舞的杨柳召唤下临波照影;紫竹园的千竿绿竹会汇聚一堂,继续去年那未竟的茶会;玉渊潭湖畔的百株杭州早樱更会奉献出春之魂,那由万朵樱花缤纷灿灼形成的景致,给那久盼春之到来的人儿。

有如随风飘飞的蒲公英种子,再后来的日子,我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密歇根湖畔。数年下来,经过獾穴之州威斯康星的严酷寒冬的洗礼,又经过风城芝加哥从湖上刮来的无尽寒风的考验,我对冬天不再畏惧和憎恶,反到体验到了等待春天的妙处。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里,二月底我曾见到被数尺深的白雪掩埋的人行道上一群嬉戏追打的学生。他们都穿着鲜艳的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在化学系的教学楼里,我还见到一位扛着滑雪板前来上课的女生。他们的脸上全没有被漫长隆冬压迫出来的沮丧。慢慢的,不知不觉中,我也学会了欣赏冬景的美丽,尝试着在安然中期待春的到来。早春二月,在这里意味着常常光临的寒流和降雪,还有与那近年股票走势相仿的老也无法上扬的气温。但是,一场春雪后的清晨,放眼望去,雪原茫茫,何处是当年印第安人的部落所在?天空虽然一片灰暗,但你能不被路边那千树万数银花开放的景致打动吗?我不由耳边响起台湾歌手费玉清的《一剪梅》:"真情象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淹没。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我对真情的体验,对雪花的喜爱,和对春天的憧憬向往在这天地一片苍茫中达到了极致。
在没有雪花飞舞,但寒风依旧的日子里,路边也有值得欣赏的景致。无论开车驰骋在高速公路,还是在乡间单行的公路上,路旁那或密或疏,或深或浅的丛林,是最令我着魔的风景。没有了夏日绿荫如盖的茂盛和深秋火红似锦的繁华,如今毫无遮拦的枝体在寒风中默默矗立,看似可怜。但你看真切了吗?他们是活着的生命!使用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想法和人交流。看,天边那密林勾勒出的画面,要赛过任何工笔的油画。那颜色岂是一个灰色所能涵盖的,分明包括了棕,橙,褐,褚,黛绿等颜色,甚至还带一抹若隐若现的紫色。细密的枝末无以计数,被风裁剪得式样别致。那数棵高大威武首当其冲的百年老树为身后的子孙挡住了多少的寒风。手挽手,这个庞大的家族成员心心相印,在风中众志成城。继续前行路过庭院深深的一个所在,寂寞的院子里,不知名的树,高矮参差,修剪得玲珑剔透,好似落魄的富家子弟,即使一无所有也不失贵族的傲慢。房后紧连一个不大的果园,株株桃树向天空伸出枝桠,仿佛在诉说往日硕果满枝的荣耀。车子路过一个自然保护区,在红绿灯前停住。右边是一片丛林的尽头,缺乏修整的林子,看去象一群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汉,在争吵斗殴中蓦然回首而被定格,包括被欺凌而倒地的那位。我猜测,春日新叶滴翠的浪漫大约不在他们费神寻思的范围内吧。落日后不多的天光下,映衬着青色的夜空,一棵棵秃秃的树,无论高矮贵贱,无论婀娜耿直,都是那么泰然自若,荣辱不惊。他们对春天的信心令我深深地感动。

等待中的春天来了吗?我想,江南的春天是位性急的不速之客,扯一把柳絮洒向空中,躲在主妇的菜篮子里就溜进了庭院。北方的春天是个贪睡的懒人,你不唤他千百声他绝不从国槐的枝头现身;而中西部的春天则是个贼精灵,你须得跨上印第安人的雪橇向那茫茫雪原深处去追寻他。

春的脚步总是那么不紧不慢。从南到北,早春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
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苏南的太湖西岸度过。春天似乎格外青睐这一片土地。记忆里刚过立春,庭院里还积雪一片,奶奶从菜市场就买回新鲜的蔬菜了。那时还没有大棚种植这一说。有两样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叫油菜,但不是开金黄油菜花,菜籽用来产菜油的那种。那厚实且深绿的菜叶子泛着油光。因其含糖分高,即使炒菜喜欢放糖的南方人也在炒油菜时省去了加糖的步骤。另一种则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菜,叫做水芹。这水芹的茎叶柄俱极鲜嫩,无论生拌或炒食都清香爽口。但它的种植说来实为不易。菜农在秋天时将种株植入深土,再在四周深挖沟渠,灌入河水。冬春时节一上市就成为抢手菜。只是不知有多少人在享受这佳肴时会想到鼻尖通红,在刺骨寒风中挖着黏土起菜的农人,和他那双手长满冻疮,在田头水沟洗菜的太太。正如白居易笔下描写的卖炭翁,这位菜农恐怕也是心忧菜贱愿天寒。对于他们来说,春天的诱惑力恐怕无法与对生计的追寻相提并论。

当江南的绿已在枝头显露时,中国北方才从千里冰封,万里雪裹之中苏醒开来。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将近十年。刚开始的几年,我几乎被姗姗来迟的春天急出病来。过了新年,依然是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一晚又一晚的呼啸北风,春天是多么遥不可及。北京市内路旁种植的多是代表古都风貌的国槐。想起来能取代国槐成为北京市树的树种恐怕不多:那样漫长的严冬,那样干冷多风的气候,沙土飞扬,百树凋零,万物萧瑟。在来自蒙古的肆虐北风稍停片刻之际,你可能会在长安街旁的人行道上瞥见一位身裹冬装,时而低头寻觅时而扬首眺望的年轻姑娘。你猜得透她在找寻什么吗?不是丢失的钱包,不是装点华美的新楼。她在努力寻找路旁草坪上任何一点代表春意的绿色,路边的国槐树上任何一点代表生命的迹象。北风吹过,白色的纱巾贴在她红色的脸颊上。多想跺一跺脚,放声喊一喊,把北风吓退,把懒惰的春天从冬眠中唤醒。因为她知道当春天终于来到时,颐和园的十七孔玉带桥会在随风起舞的杨柳召唤下临波照影;紫竹园的千竿绿竹会汇聚一堂,继续去年那未竟的茶会;玉渊潭湖畔的百株杭州早樱更会奉献出春之魂,那由万朵樱花缤纷灿灼形成的景致,给那久盼春之到来的人儿。

有如随风飘飞的蒲公英种子,再后来的日子,我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密歇根湖畔。数年下来,经过獾穴之州威斯康星的严酷寒冬的洗礼,又经过风城芝加哥从湖上刮来的无尽寒风的考验,我对冬天不再畏惧和憎恶,反到体验到了等待春天的妙处。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里,二月底我曾见到被数尺深的白雪掩埋的人行道上一群嬉戏追打的学生。他们都穿着鲜艳的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在化学系的教学楼里,我还见到一位扛着滑雪板前来上课的女生。他们的脸上全没有被漫长隆冬压迫出来的沮丧。慢慢的,不知不觉中,我也学会了欣赏冬景的美丽,尝试着在安然中期待春的到来。早春二月,在这里意味着常常光临的寒流和降雪,还有与那近年股票走势相仿的老也无法上扬的气温。但是,一场春雪后的清晨,放眼望去,雪原茫茫,何处是当年印第安人的部落所在?天空虽然一片灰暗,但你能不被路边那千树万数银花开放的景致打动吗?我不由耳边响起台湾歌手费玉清的《一剪梅》:"真情象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淹没。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我对真情的体验,对雪花的喜爱,和对春天的憧憬向往在这天地一片苍茫中达到了极致。
在没有雪花飞舞,但寒风依旧的日子里,路边也有值得欣赏的景致。无论开车驰骋在高速公路,还是在乡间单行的公路上,路旁那或密或疏,或深或浅的丛林,是最令我着魔的风景。没有了夏日绿荫如盖的茂盛和深秋火红似锦的繁华,如今毫无遮拦的枝体在寒风中默默矗立,看似可怜。但你看真切了吗?他们是活着的生命!使用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想法和人交流。看,天边那密林勾勒出的画面,要赛过任何工笔的油画。那颜色岂是一个灰色所能涵盖的,分明包括了棕,橙,褐,褚,黛绿等颜色,甚至还带一抹若隐若现的紫色。细密的枝末无以计数,被风裁剪得式样别致。那数棵高大威武首当其冲的百年老树为身后的子孙挡住了多少的寒风。手挽手,这个庞大的家族成员心心相印,在风中众志成城。继续前行路过庭院深深的一个所在,寂寞的院子里,不知名的树,高矮参差,修剪得玲珑剔透,好似落魄的富家子弟,即使一无所有也不失贵族的傲慢。房后紧连一个不大的果园,株株桃树向天空伸出枝桠,仿佛在诉说往日硕果满枝的荣耀。车子路过一个自然保护区,在红绿灯前停住。右边是一片丛林的尽头,缺乏修整的林子,看去象一群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汉,在争吵斗殴中蓦然回首而被定格,包括被欺凌而倒地的那位。我猜测,春日新叶滴翠的浪漫大约不在他们费神寻思的范围内吧。落日后不多的天光下,映衬着青色的夜空,一棵棵秃秃的树,无论高矮贵贱,无论婀娜耿直,都是那么泰然自若,荣辱不惊。他们对春天的信心令我深深地感动。

等待中的春天来了吗?我想,江南的春天是位性急的不速之客,扯一把柳絮洒向空中,躲在主妇的菜篮子里就溜进了庭院。北方的春天是个贪睡的懒人,你不唤他千百声他绝不从国槐的枝头现身;而中西部的春天则是个贼精灵,你须得跨上印第安人的雪橇向那茫茫雪原深处去追寻他。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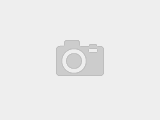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