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一九二0年出生在彩衣街老宅,直到三七年逃难才离乡。小时候,我并不觉得家乡有甚么好。一道破破烂烂的城墙,一条条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道,弯弯曲曲的一人巷,堆满街头巷尾的垃圾,有甚么好?甚么「三分明月二分在扬州」,甚么「烟花三月下扬州」,甚么「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仿佛都是无稽之谈。
芦沟桥炮声一响,几个月后日寇兵临城下,我上过五年半的扬州中学宣布解散,全体师生齐集树人堂,合唱《松花江上》,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全场泣不成声。会后,大家纷纷离校,我也加入了流亡学生的队伍。谁料到,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就从此漂泊天涯。十几年当中,跑过不少中外名城,我反而日益怀念我那「一无是处」的故乡了。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从芝加哥大学兼程回国,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游子还乡,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为人民服务了。我把寡母从扬州接到北京同住,暂时就不急于还乡。谁料到,一入彀中,一切便都身不由己。先是我中了「阳谋」暗算,发配北大荒,老母和妻子儿女被赶到合肥。及至「文革」十年浩劫,红卫兵勒令我的老母离城,这时我已身为「牛鬼」,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家在离家十五年之后又孤身还乡。
一九六八年二月,接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我立即请假去奔丧。经过一昼夜车船的折腾,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卅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声﹕「故乡,你的游子回来啦!」可是故乡变化不小,乍一看几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尘满面,鬓如霜」,形同陌路。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进们后才知道经过房改,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听堂弟妹们说,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糖尿病加剧致死。灵停在一间黑屋子里,老人家在那里面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
第二天一早,我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入土为安。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从小是孤儿,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被嫁给我父亲当填房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赋闲,家里靠典当过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还不让失学,谈何容易!后来,她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国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无奈十七年来,老人家受我株连,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多年来,虽然说不上为扬州魂牵梦绕,我还是常常惦着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来的,磨难还没尽头哩。当年那些恐惧和梦想,它们曾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背井离乡,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如今,梦想早已破碎,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游子还乡仿佛是一场醒不了的噩梦中的插曲。
安葬后第二天,弟妹们忙于「闹革命」,我独自到大街小巷去走走,看看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彩衣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小时从来没听说过,现在也无心去打听。只觉得这彩色斑烂的名字,对两旁贴满大字报的长街,真是绝妙的讽刺。我想起当年那些摆摊子的手艺人,或是用面团,或是用梨膏糖,作成形形色色的神仙人物,孙悟空啦、猪八戒啦、哪咤啦、托塔李天王啦,一个个神采飞扬,五色缤纷。那些彩衣神仙曾为我孤寂的童年添过多少生趣,画过多少好梦!

一个过路的胖男骇好奇地睁着大眼睛朝我看,我便问他还有没有做面人儿和糖人儿的,他笑呵呵地说﹕「一听就晓得叔叔是外地来的。扫四旧早就把他们扫光了。」
我说﹕「你不觉得可惜吗?」
胖孩子说﹕「那有甚么法子!文化大革命嘛!」
我说﹕「你说得对。你的扬州话说得真好听。」
他说﹕「扬州人不说扬州话说甚么?」
我笑着用扬州口音说﹕「我也会说扬州话。」
小胖子又乐呵呵地说﹕「叔叔说的又不像。」
我突然感到失落了,我多么羡慕那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的诗人。(上)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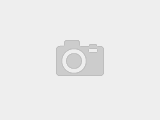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