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晓雯的上一部作品《浮生二十一章》以小人物的命运为聚焦点,以“人物素描”的简洁方式写作,不像一般读者习惯的短篇样式,读来别有意味。新书《朱三小姐的一生》则更“像”短篇小说,也是任晓雯用以回答“短篇小说何为”这一问题的具体方式。
新书共六个故事,有的写一个人的一生,如《朱三小姐的一生》,有的则集中在充满戏剧性的事件上,如写母亲不愿为儿子捐肾的《换肾记》。故事跨越的时间有长有短,冲突或激烈或相对平缓,但其中都有“幽暗摇曳的人性”。
六个故事还另有一处共同点:疾病缠绕,深刻影响着人的命运。对此,任晓雯在本次采访中说:“我们活着,为的是喂养身体,包裹身体,满足身体的欲望,维护身体的运转,修补身体的残损。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是呼吸着的行尸走肉。在生命的某些时刻,灵魂会面对如此巨大而盲目的消耗,发出一声刺耳的惊叹。而我的小说正是想写作这样的时刻。”

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著有《好人宋没用》《阳台上》《生活,如此而已》等。曾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全国中篇小说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奖等。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法文、瑞典文、意大利文等。作者供图。
文学的价值在于“整全思考人类生命秩序”
新京报:在小说集序言《短篇小说何为》中,你谈及长篇小说的一些现状。在阅读近几年的国外作品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一部引起好评的小说,可能仅仅关注一个具体问题,比如种族、性别、家庭、战争。”这种带有具体的、相对单一的问题意识的长篇小说,似乎很受奖项的青睐。这一现象背后有社会因素导致的某种必然性吗?你认为这种写作遮蔽了什么?是否暗示出当代部分写作者认知和思考能力的局限?
任晓雯:我认为这个问题存在,但不是普遍存在。我读到过不少当代西方超越议题的优秀小说,比如美国作家唐娜·塔特的《金翅雀》,其中关于生命脆弱性的描述令人迷醉。奖项是人评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趣味。我们当然可以说,有野心的文学家是面向永恒写作的,而经典文学作品的流传也一次次超越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变。但是,在当时当地,就一部小说而言,其出版后的反响,必然受非文学因素限制。
有时候是商业和市场,有时候是社会风气。这不是写作者的问题,甚至不全是出版商、评论者和文学奖评委的问题。当我们回顾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品,会看到在它们的“当时当地”,有的被反复退稿,有的出版后恶评如潮,有的则短时间内默默无闻,时隔很久才被重新发现。被遮蔽、被高估、被遗忘、被重新发现,都不是新鲜故事。著史者有兴趣可以去梳理,但写作者的目光最好还是看往更高远的方向。
新京报:在这个所谓“碎片化的时代”,写出《安娜·卡列尼娜》这样“整全思考人类生命秩序的作品”,是否已不可能?如不可能,原因在哪里?此外,是否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有写作者想用长篇小说的方式思考人类善恶、正义、罪罚、宗教等问题,也难以超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以致后来的写作者更倾向于选择回避?
任晓雯:“碎片化的时代”这个用语容易让人以为是指信息的碎片化,我更愿意使用的表述是“人类知识细分的时代”。日益臃肿的学术规范,反复细分的学术科目,让人离最本初的命题越来越远。这样的状态当然容易让人迷失,但我觉得不至于“不可能”再去思考。作为有灵魂的人类,我们时刻面对这些命题。我们必然思考为何活着,怎样活着,必然思考死亡。哪怕是最愚钝的人,面对生死的巨大撞击,都会有难以言述的闪念。我觉得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此,就在“整全思考人类生命秩序”里。否则为什么要搞文学呢,写几篇学术论文和时评就得了。
你问及另一个问题——是不是现在的写作者很难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式来超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认为是的。不仅是这两位,还包括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等一系列古老名字。但相比于选择回避,我更愿意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局面。我在《朱三小姐的一生》这本书的万字前言里,也部分表达了这一思考。
新京报:你喜欢哪些短篇小说家?原因是什么?好的短篇小说应该是怎样的?
任晓雯: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家有奥康纳、辛格、契诃夫、巴别尔、海明威、克莱尔•吉根等。好的短篇小说应该像诗歌一样。它对语言的要求比长篇高,它要有对读者心灵一击而中的能力。


《朱三小姐的一生》,作者:任晓雯: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
“写作是以刻苦的态度做一件游乐之事”
新京报:序言中还提到一个问题,关于“政治正确”。现在“政治正确”似乎越来越多,有的作品因此被下架,有的则受到更多关注。具体到文学,你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正确”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政治正确”也不是这几天,甚至不是这几年的事情了。我硕士研究生时代的导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很有研究心得。我跟着读了很多西马、后现代的东西,并把当时颇为时髦的文化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甚至在2001-2004年在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担任过特约研究员。
由于那几年的浸淫,我对这套西方左派话术算是熟稔的。性别、种族、殖民……它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演变脉络。但是我不当学术青年已经很久了。二十年前,自打我一头扎进文学,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努力把这些理论概念从头脑里剔除出去。原因很简单,它们在和文学打架,它们有着和文学不同的逻辑。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是依靠理论概念来写作的,也没有真正的文学是作为理论概念的例证和补充而存在的。所以,尽管读者和评论者可以有各种阐释和态度,但对于写作者而言,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新京报:序言中提及托尔斯泰时,说到“现实主义手法”。近三四十年,多种写作风格、样式的作品被翻译进来,从中可以发现,对写作进行创新的意愿在一些写作者那里涌动。你如何看待“现实主义手法”?如何看待对写作形式进行(刻意)创新的意愿?《朱三小姐的一生》,包括之前的《好人宋没用》《浮生二十一章》大概是属于现实主义写作的,你是自觉地在坚持这种写法吗?
任晓雯:“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宽泛而有生命力的概念。加西亚·马尔克斯构建了最光怪陆离的小说世界之一。他写一个漂亮女人裹着毯子飞到天上去了,却仍坚持说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他认为神奇或魔幻只是每日可见的事实,决不是作家“制造的”、“改变的”、“写得不可认识的”:“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本版节选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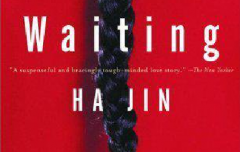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