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几何时,大粪是种好水稻的一个宝,大家不得不依赖于挑粪来增加农田的肥力。每当农耕,所有家庭的男女老少都要投入到这项繁重而又充满臭气的劳作之中。
清晨的第一丝曙光刚刚洒在大地上,田埂上的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大粪的气息。人们像是按照默契一般,在天亮前便已经挑了好几担大粪倒到田里了。只见人们挑着粪桶,往返于猪圈和稻田之间。一时熙熙攘攘,颇为热闹。挑粪沤肥,在当时,那是农田丰收的希望。“没有大粪臭,哪来稻米香?”这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我挑着粪桶跟在父亲后面。我虽然只挑了两个半桶,却还是感到很吃力,摇摇晃晃地走着。大粪在桶里极不“安分”,你越晃,它就越溅。几乎你晃一下,它便溅几点粪水到你身上。一担挑下来,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全是粪水的痕迹,甚至连嘴唇上都溅了好几滴。反正一路上都是大粪的味道,又脏又臭。
后来,父亲在我的粪桶里放上南瓜叶。粪水一下子似乎收敛了性子,再也不那么任性地溅到我脸上了。我依旧在路上摇晃着,看着“老实”的粪水,我不禁在心里嘲讽它:“你不是很神气吗!有本事你溅我呀!”
当然,嘲讽归嘲讽,估计大粪也听不见。你说得再解气,大粪还是大粪。它不会少一分脏,也不会少一分臭,更不会减轻一分重量。倒是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从脸上流到脖子上,又从脖子淌到前胸后背。时间一久,汗味和粪味掺在一起了,好闻你也得闻,不好闻你也得闻。
溅到脸上的粪水无伤大雅,汗流浃背也无妨。最可气的是难走的路。我家有一丘田在一个比较远的小山谷里。小路崎岖不平不说,还夹杂着荆棘。那时候,都是赤脚走。大人的脚底长着厚厚的老茧,踏上去不会有事。而我走在那条路上,却是如履薄冰。生怕一脚踩在荆棘上,而弄得脚破血流。但是再不好走也得走。看着前面像铁人一样的父亲,我咬咬牙,鼓足勇气往前走。有几次被划伤了,我强忍住泪水,硬是挺了过去。一点皮外伤也算不上什么,在泥巴里踩几天,自然就好了。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
星霜荏苒,往事也已飘远。如今,农村已很难看得到挑粪的身影了。而我小时候挑粪的经历,却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那一滴滴粪水、一串串汗珠、一道道伤痕,化成了我永远坚持向前的力量的源泉。
作者简介:尹晓华,湖南省茶陵县人,农民工,爱好文学,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诗词学会会员,有作品散见于《中华辞赋》《中国审计报》《中国楹联报》《山西晚报》《湖南工人报》《浙江老年报》《株洲日报》《温州晚报》《长沙晚报》等百余家。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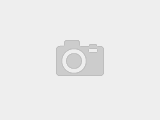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