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末日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他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生别常恻恻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年青时候,未经丧乱,哼这两句词只感到一点淡淡的哀愁,并不体会离别之伤痛。后半辈子,苟全性命于乱世,亲友往往天各一方,离多会少,久而久之大家对生离死别也麻木了。劫后余生,浪迹天涯,「往事回思如细雨」,有时反倒不免黯然神伤。
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在北京,历时大半年的「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三月二十一日,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对全院「右派分子」的处理。小小学院,师生拢共不过三、四百人,榜上有名的竟有二十余名。我名列榜首,当然恭逢其盛,妻子也得在座陪绑。我受到一等一级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当天正赶上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右派」属「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上仍享有公民权,奉命参加投票。大会收场后,二十几名人犯被一位大义凛然的小干部叫到一起,先听他声色俱厉地教训一通,然后排成双行押解前往大食堂,行使共和国公民的选举权,为独一无二的候选人投「神圣的一票」,证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
回宿舍的路上,熟人相逢都不屑一顾。我出身寒门,从小就习惯世态炎凉的滋味,因此并不感到意外。回到家中,妻子递给我一杯清茶,我接过来有气没力地往沙发上一靠,看到白磁杯上的七个黑字,「一片冰心在玉壶」,感到心里一片冰冻,真不知言从何起。可巧丁儿趔趔趄趄地摸了进来,给我解了围。丁儿不久前刚过了两周岁生日,尽管家中大难临头,妈妈还是为宝贝儿子包了饺子。
「爸爸,大爸爸,」他边走边嚷,「我生日那天,你说天一暖和就带我上动物园看大象。早起阿姨带我上颐和园,树上都开满了花。你快带我去看大象吧!」我把他搂进怀里,强笑着说﹕「小丁丁,快啦,快啦!爸爸一得空就带你去。」他嘟着小嘴说﹕「你可不能骗我呵!」我说﹕「爸爸甚么时候骗过你?你等着瞧吧。」夜间,孩子睡下后,妻子说﹕「这孩子别的甚么也不要,只惦着跟你去看大象, ……」我说﹕「一天到晚,不是批斗,就是劳动,哪有空啊?眼看我该走啦,说甚么也得带他去一趟,你放心吧。」妻子眼泪汪汪的,我不知说甚么是好。
(三)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关注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精彩内容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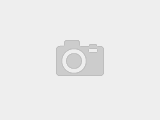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