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是部分华语小说奖授奖辞
赵本夫《天漏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 刘稚
《天漏邑》是赵本夫先生厚积薄发匠心独运的一部力作,是近年长篇小说一个令人振奋的收获。小说融神话故事、历史传奇和现实人生于一炉,叙事空间多维互补,大跨度转换有条不紊,众多人物形象鲜活而立体。历史天命的探询,现实人生的讽喻,复杂人性的拷问,共同诠释了“天漏而人不可以漏”的基本主题,直抵中国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立意高远,气度不凡,为战争历史小说别开新面。
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 《钟山》 2017.1 责任编辑 贾梦玮
这是一个上海人在美国的故事,是上海与纽约的“双城记”。王安忆作为一个炉火纯青的作家,面对任何题材都能从容不迫,凡俗人生,却展开不同寻常的讲故事风格。不依赖圆熟的技巧或戏剧化的细节,转向中国古代小说简约的白描风格,三言两语即画出人物神韵。文字耐人寻味,偶尔有所吞吐,似乎故意暗中约束,借此激发读者想象的张力。贯穿于作品始终的伤感,是沉潜的生命律动。
张悦然《大乔小乔》 《收获》2017.2 责任编辑 程永新 走走
一次意外的流产,灾难与不幸降临到了一个普通家庭,大乔小乔和她们的父母陷入巨大焦虑和痛苦之中,两代人的命运也因之改变。面对沉重而复杂的主题,张悦然通过平静而坚实的叙事、内敛而深沉的反讽,细致描写人物悲惨的内心世界,尖锐揭示生活的荒谬感和悲剧性。作品不仅表现出高度的伦理思索,而且显示了成熟的叙事智慧,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在人生探求和叙事创新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年轻作家。
莫言《天下太平》 《人民文学》2017.11 责任编辑 徐则臣
小说设置两个套叠的文本:从孩子的眼睛记述两个贪心的打鱼人故事;用奇异的老鳖来讽喻人与自然的冲突。故事一波三折、吊诡奇崛,寓意丰富、藏而不露。“天下太平”出现在一只鳖背之上,似有古老的依据,却释放出强烈的现实寓意:环境的危机与风俗的败坏,使自古而然的农耕渔猎尽失其据,令人寝食难安。小说强烈的现实关怀,感性丰腴的文字质地,细微饱和的叙述笔法,宣示着“讲故事的人”莫言的不同凡响。
樊健军《穿白衬衫的抹香鲸》 《青岛文学》2017.4 责任编辑 章芳
抹香鲸来自大海,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则来自城市。在林场,他的格格不入最终酿成了悲剧。小说充满对现实的隐喻,故事冲突饱含荒诞感,可贵的是,隐喻性并未耗损其质感,荒诞反而助力了深刻。作者试图用优美的散文笔法唤起象征性解读,以呈现复杂性的姿态反抗简化,使个体最终超越比自己更广阔的东西。抹香鲸之死,成为林场孩子们心中不可磨灭的、象征悲悯和救赎的龙涎香。它或许能唤醒人们心中的龙涎香,让我们都保有一份真挚与警醒,使世界更具关怀和温情。
双雪涛《北方化为乌有》 《作家》2017.2 责任编辑 王小王
双雪涛用富有魅力的人物,直白揭示了生活的本质真实,让我们触碰到坚硬的质感,同时也为人物的塑造发挥到极致创造了氛围。作者叙事能力与风格、大大提升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字里行间,深含北方中国的忧虑和伤情。双雪涛是一个不作伪的书写者,一个能够把一桩案件化为小说的完美故事作者,小说之成功不仅因为独特的题材和出色的语言,也与作者领悟生活,发现故事背后的广袤历史背景密切关联。
微小说作家奖得主 蔡中锋
蔡中锋在多年的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打破了历史、典故、奇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隔阂,运用想象力构思出各种不同题材的微小说。他的作品切入角度巧妙,结构展开各具特色,既能采用“三一律”结构,用三个或三个以上层层递进的情节或片段突出一个主题,又能突破“三一律”,拓展创设微小说结构的广阔空间。语言平和朴素,文字收放自如,以不足千字营造出极大的内涵和张力,让悬念迭起的故事真实自然。
作家获奖感言:
长篇小说获奖作家:赵本夫
《天漏邑》获得2017年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三十七年前,我有幸以处女作《卖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纪事》同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北京颁奖大会期间,游览北海公园,在林斤澜、刘绍棠先生的热心提议和见证下,在北海公园里拜汪先生为师。当时,我退后几步,虔诚地向先生鞠了一个躬,汪先生却上前抓住我的手哈哈大笑,说咱们是同科进士,以后互相学习!后来的很多年,汪曾祺先生对我关爱有加,给我写信鼓励,给我寄送他的作品集,给我作画题字。每次见面,都会聊一聊。十年后,在得知我举家迁居南京时,他第二次给我画了一幅画,并题了一首诗——
“人来人往桃叶渡,风停风起莫愁湖。相逢屠狗勿相讶,依旧当年赵本夫。”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期望。
南京是个衣锦繁华之地,不管人来人往,风停风起,要守住自己的本色,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
可以说,汪曾祺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么多年,从他生前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作品中,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两个字:从容。在汪先生那里,从容是修为,是定力,是境界。
“从容”二字,也非常契合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
我虽然从少年时代就立志文学,但直到1981年,也就是三十四岁时,才发表第一篇作品。应当说很晚了。这是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极左思潮仍然笼罩着文坛。我并没有着急,一直在读书、积累、思考、等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正式动笔。上世纪九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目不暇接,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还是慢慢道来》。我的长篇小说“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从构思到完成写作,用了二十三年。这部《天漏邑》也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我希望它们是从容的作品,而不是急就章。
这次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以汪先生的名字命名,必定带有鲜明的汪曾祺小说美学品质。每一位作家对社会人生都有自己的思考。哲学告诉我们怎么理解世界,文学告诉我们怎么和世界相处。汪曾祺先生说过,文学还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我愿以这部作品作为对汪曾祺先生多年关爱的一次汇报,希望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中篇小说奖:王安忆
感谢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评委给我荣誉!
此时此刻,想起许多往事,记得一九八七年在香港维多利亚游艇上,我们一群——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拥着汪曾祺问这问那。我们问短篇小说是什么?回答说,就是将必要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又问,长篇小说是什么,汪老回答,就是把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可不是吗!汪曾祺老一生写下无数短篇小说,却未涉猎长篇,就是说,他都是在说必说不可的话。今天,获奖的《向西,向西,向南》是一个中篇,正介乎于必说与不必说的话之间,不知道汪曾祺会不会喜欢?
汪曾祺还对我说过,要学习北方语言,南方的语言不够好。我去过汪老的家乡高邮,地处南北交集,语言亦南亦北。我想汪老是有资格评判语言的优劣的,不是地方偏见,而是,小说家总是在找最优质的表现,去芜存精。重要的是,汪老不是要我从书本上学,我们的书面语言就是北方语言,他是要我从民间学习,小说的语言是动态的,而民间生活最是生动活泼。
汪曾祺曾经向我描述他的写作:喝二两酒,吃点豆干,微醺,提起笔,真美啊!
精神劳动竟然会生发感官享受,除非深知其中乐趣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的。我正向这境界靠近,距离尚远,但亦步亦趋,文学的世界逐渐呈现出人生的喜悦。
谢谢大家!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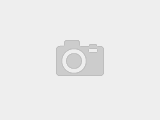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