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走到打字室向小组长报到。她跟我握手,笑着说欢迎我参加打字室工作。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的和一丁同年 ,我们俩也许有共同语言吧。提到她爱人,一位俄语讲师,是外语系的党总支部委员,她脸上有得意之色。她本人是俄文打字员,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年长的英文打字员老陈,随即指着一台古老的Underwood牌的台式打字机,对我说:“这是你的,一直在等你来!大跃进热火朝天,工作做不完。老陈忙得不可开交。你今天可以开始工作吧?”她边说边交给我打蜡纸的任务。离开北京之前,我以为从此与蜡纸再见了。谁会想到,跑了千百里路,我又干起不是本行的老行当来了。
和全国各地一样,安大也是“政治挂帅”。政治学习、大会小会占用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就任意推迟,星期日经常放卫星。工作这么重,还有一个小孩要喂奶,一个大的要抚养,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吃不消。小组长,绰号“小辣椒”,原来又是一个“小左”。她总找我的岔,监视我的行动,甚至于上厕所也不放过。宁坤写给我的两周一次的家书也要交给她检查。她是职员政治学习小组长,开会发言时往往把矛头对准我。
“小辣椒”还不时专门为我召开小组会,帮助我加速思想改造。她责成我必须“暴露思想”,争取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我总首先感谢党组织和小组长领导下的同志们对我一贯的关怀。然后我就坦白承认,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喂小的、管大的、烧饭、洗衣、搞卫生,我根本没有精力想什么,脑子往往一片空白。“小辣椒”总会批评我不肯暴露坏思想,因此妨碍思想改造。“你的教授爱人被划为极右分子,又送去劳教,你怎么可能不对我们的党心怀不满?只要你一天不和他划清界限,你就决不可能真正体会我们的党对你、对你爱人,是如何宽大。你必须首先暴露思想,否则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就一定会继续毒化你的脑袋,那是十分危险的。”她对我提出严正警告,仿佛我已经走上通往地狱的下坡路了。我明白,她整我可以向党组织邀功,也有党组织作她的后台,我无法和她较量。她一再重复我早就领教过的 “治病救人” 的口号,启发我自投罗网。但我也记得一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身为右派家属,挨批、挨整、被歧视、被孤立,已经司空见惯,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逐渐泰然处之了。

日常生活也成为茹苦含辛的挣扎。1959年秋季,大跃进的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饥荒,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党组织宣称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大跃进的后果。同时,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逼债,不仅为那些苏方以“兄弟般的援助”建设的工厂,而且要为朝鲜战争中支援中国志愿军的军火,以食物偿付。于是,偿债列车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物源源不断运往莫斯科。中华儿女只有挨饿的份儿了。1959年夏季开始,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减到二十四斤,平均每天八两。供应的品种主要包括:山芋乾、山芋面、玉米面、高梁面。大米和小麦面只有在逢年过节小量供应。食油从每月半斤减到二两 。猪肉和鸡蛋,起初少量定量供应,后来干脆完全绝迹了。营养根本谈不上,大家开动脑筋怎样把八两粮食做出来显得多一些,哄骗自己。我一个接一个试了党报上刊登的各种烹饪法,也无济于事,肚子还是永远饿得难受,听丁丁总嚷嚷肚子饿更加难受。出卖食物的黑市公开露面,但价格高得让我无法问津。我的体重不断下降,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奶奶因营养不良糖尿病加重,早就回北京住到宁慧姐家去了。
我整天上班,而且上班时间越来越长,还要带两个小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丁白天上幼儿园,由我接送。一毛没人管,我只得雇一个阿姨带她,帮助做点家务事。每月工资二十二元,占我工资40%。 简直是发疯,可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日子虽说难过,但我觉得,宁坤被迫流放,我怎么样也得咬紧牙关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而且,谢天谢地 ,没有发生更坏的情况。
小高阿姨是合肥市郊区肥东县乡下的农民,一副朴实的农民面孔,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我们相处得很好,也许因为我们俩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吧。我把孩子和家交给她,很放心,相安无事过了好几个月。后来,一天上午我正在打字室上班,保卫科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又怎么啦?我有些紧张回到屋里,发现一名保卫科干部坐在外屋一张小折叠桌旁边,小高低着头站在他面前。
“怎么回事儿?” 我惊慌地问道。
“你让她自己给你说吧。” 保卫科干部冷笑着说。
“小高,你说吧。”
她突然掉转身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
“我是罪人,李老师。” 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待我像自家姐妹,我反而对不起你。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干这种事。要是我再干,你就杀了我。李老师,请你饶了我吧,救救我吧。你一定会饶了一个可怜的农民吧......” 我感到困惑,也感到难堪。我自己是一个入了另册的人,如今眼看一个如此悲痛的姐妹,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跪在我脚下求情,我真受不了。
“小高,快站起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我一边劝她,一边伸出手把她扶起来。
她哭得更凶,一开口就语无伦次。保卫科干部插话,告诉我一名巡逻的校警抓住她把我家的食物和衣服从校园围墙的墙头扔出去,由站在墙外的她嫂子接着。我本来常认为自己穷得像乞丐,想不到这个农家妇女却还来偷我!保卫科的人说,看来她是初犯,给予宽大处理。不过安大校园里她是呆不下去了。这可难为我啦!让她走,一毛怎么办?不让她走,我就是在家里窝藏小偷?天哪,为什么这种事非得落在我头上?
“如果她现在就走,我孩子没人管。”我考虑了一下以后对保卫科干部说。“我想留她在我家,等我解决了孩子的问题再让她走,当然要保卫科同意。”
“李老师,你担风险吧。”他同意了。“不过,你要承担责任,如果她再犯案。”
保卫科干部一走,我让她先洗脸,然后在单人床上坐在我旁边。我不能决定对她说什么。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她这样一来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如果她真的缺什么,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讲?我再穷也会尽力帮她的。现在我一定要让她明白,偷盗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她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那样我是否会对她作出过分严厉的裁判?何况我有什么权利裁判她呢?仅仅因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穷农家妇女偶然拿了我几样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不,我不能那样教训她,我得为她着想。她帮我带孩子、做家务,在我孤单时跟我作伴。现在她碰到了困难,该是我帮她了。
(29)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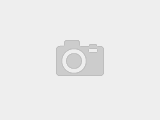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