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姓冒,冒充的冒。我冒充是教授、诗人、学者,但我只是个骗子。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小官,我接受过日寇占领时期汪伪政府一个名义。我一向过着腐朽的生活。今天早上堆在篮球场的东西,大多数是我家的。所有的国画、书法条幅、摺扇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四旧。其中有一些是父母传下来的,我一向当作传家宝珍藏。我多年来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和品味的腐蚀,现在我可以把这些四旧看作我肮脏的灵魂的罪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胜过在座的任何人,因为我罪大恶极,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我一向钦佩伟大领袖毛主席辉煌的诗词,相比之下我自己的诗只是垃圾。但是现在我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些宏伟诗篇,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已老态龙钟,但我仍然心甘情愿通过艰苦劳动改造自己。”
我觉得冒教授的检讨也算得上一篇冒充沉痛的杰作,差点儿忍不住以小组长之尊问他,既然“一死”不足以赎罪,他打算死几回?不过我倒真心希望红卫兵不会胡闹到真的把他那些珍贵的艺术品一股脑儿扔进一堆篝火化为灰烬。前两天,红卫兵要放火烧图书馆,幸亏馆长急中生智,对他们说1958年夏“伟大领袖”驾临新建的安大曾亲临图书馆视察,他们才悻悻而去。可是,在市中心,一帮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一位老年学者家中,把他毕生收集的三千册中国古典文学善本书统统扔进他们在门前生起的一堆篝火,老人家痛不欲生,从二楼书房的窗口朝着篝火跳下,当场毙命。红卫兵见死不救,反而当众宣布:“死者顽固不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打成现行反革命。”虽然与京、津、沪等大城市相比,省会的红色恐怖是“小巫见大巫”,无辜惨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二天中饭后,外语系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我家查抄四旧和反革命罪证。四人小队由小包带领,他是我教过的男生,两年前毕业后留下当助教。他平常见我总是未语先红,今天却绷着脸对我说:“巫宁坤,把你从国内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给我”。我说:“我们没有保存旧信的习惯。”那是我们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吸取的教训。于是他下令让我开一个和我通讯的亲友名单。我照办。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柜,仿佛十一年前肃反时在南开大学演过的旧戏又卷土重来。几小时后,抄家小队收兵,带走几件可疑物品。一件是我的Smith-Corona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有十五年前我从旧金山上船回国前李政道用白漆写的“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字样。还有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后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国朋友伯顿夫妇的合影。另外还有我的柯达布朗尼儿童照相机、两个从旧唱机拆下的电子管、一个一百瓦灯泡、和几条旧领带。连我们的英国自行车也不由分说被我班上一个男生强征去“闹革命”了。
红卫兵总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动交出属于四旧的书刊文件和其它物品,否则格斗勿论。我选出了一堆中、英文书刊,其中包括我在曼彻斯特学院1948级纪念册《曙光》,这名字在当时倒有点反讽的意味,另外还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学位证书。我还得自己把它们送到一个新成立的四旧存放室。在去交四旧的路上,我经过起义外交官老王夫妇住的公寓楼。王太太正在从三楼一个窗口大哭大喊:“我不是地主!我是老王的爱人!我要收回我们值钱的东西!”路上有几个人抬头往上看,有人说:“这女人疯啦。”我走到四旧室,发现里面已经放满了图书、艺术品、衣服等等,便自我安慰我的损失和别人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听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损失,我却吓呆了。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间宗教专家,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种稀有的“宝卷”,却被街道上的红卫兵用三部板车拉走了,下落不明 。
随后几天,在外语系带动下,各系红卫兵纷纷对本系采取了类似的“革命行动”。全校牛鬼随时随地被揪斗,其余时间在校农场劳动,或干脏活,例如从粪坑把大粪抬到农场。与此同时,大部分革命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免费旅游。旅游客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带回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除了那些神化“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的文字,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疯狂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了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的总头目。红卫兵深深卷入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全国分裂成两大“造反派”。时隔不久,派系之间在大字报上的唇枪舌剑发展成武装斗争。到了1967年夏,全国实际上已处于内战状态。
校园和合肥市一样掌握在两个势不两立的武装造反派手里。男女小青年成群结队,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拿着大棒或匕首,在大街上游逛,搜索敌对派别的成员。骇人听闻的传说不胫而走。市民没有必要就不出门,后来干脆到外地去避难。怡楷和我不知怎么办,就到火车站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发现站台上人山人海,眼前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不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就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不难想象列车穿过第一个隧道时坐在上面的人就会摔死,后来听说果真如此。这番景象让我想起,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逃难时乘的火车,但哪怕在那时候也没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火车顶上。我们当当机立断,我们只能就地凑合着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们的性命去冒这种危险。
一旦党的领导瘫痪,“革命小将”要么外出免费旅游,要么忙于打派仗,牛鬼也就没人管了。校园空荡荡的,夜晚一片死寂。有一天,怡楷找回了我们的英国自行车,她是在一栋男生宿舍发现的,扔在墙角的垃圾堆旁,毁得面目全非,好像一个整得遍体鳞伤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在两个大缸里储满了饮水,用所有的票证尽量储备食物。
燃料成了大问题。时值盛夏,煤球停止供应。煤球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一样,也停止生产,有的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一派,有的去周游全国闹革命。走投无路,我和住在我楼上的一个年轻人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车去十几里外的一个煤场,但愿能拉回一车煤球烧炉子。煤场挤满了人和平板车,我们一到就听说我们得自己动手做煤球。排队等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付了钱,开了票,去领每户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然后是抢一辆小铁板煤车,装满煤灰,沿着一块跳板,推过去,倒进一台煤球机。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二人才光着上身把四百斤宝贵的煤球拉回家。虽然全身黑汗淋漓,我感到一种反讽的满足,有气无力地对一同拉煤回来的年轻人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怡楷和一丁帮我把两大筐煤球抬回家后,我蹲在小厨房里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龙头下面,用水冲洗我满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么睿智的先知能告诉我,这片国土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者走火入魔,还是一个民族正在经历什么神秘的危机 ?
1968年2月下旬,我收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幸而两派的小将忙于打派仗,顾不上对牛鬼专政,我才能向系主任请假一周奔丧。多年来,我常常惦着回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
(49)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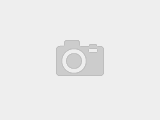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