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早晨,我们排着队,经过虎视眈眈的警卫和他们的刺刀,离开分场大院,前往田野劳改。值日的队长把出工人数告诉警卫班长,班长一个一个点数人头放行。傍晚收工返监,班长重新清点人数。政治学习,不如说是批判会,占用晚上的时间。队长们一个个都是铁板面孔,俨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他们和李队长毫无相似之处,李队长完全够不上这个制度的化身。名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我过的和感受的却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囚徒的生活。
在移监之前,我已经从《人民日报》报道的字里行间猜出国家形势并非大好,但是我无从知道情况坏到什么地步。我们到达三分场那天,曾经指望吃到一顿一般给新来的人吃的好一点的伙食。不料我们吃到的却是萝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汤。汤里没有一个油星子,饭后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兴,因为东北太冷不种山芋。还有些人说大伙房没空给我们做一顿好饭,但迟早会吃到的。当天晚饭吃的是同样的东西,随后两天也一样,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两餐。第四天,清汤里没有山芋,增加了萝卜叶子。我们觉得肚子总是饿,但是照样每天下地劳动。
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装上卡车运往北京。每一颗大白菜都装车之后,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我怯生生地问他:“干什么用?”他答道:“你们明天的伙食。”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装进箩筐,准备送往伙房。队长喊道:“回来。你们为什么没把乾菜叶捡起来?” 我感到莫名其妙,又问他:“干什么用? ”队长胸有成竹地说: “你们春天吃。” 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双手按他说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说,缺少食物,成为我们的心病。难友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他们吃过的好东西,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乱坠,还煞有介事地交换食谱。他们互相倾诉夜以继日的饥饿如何煎熬他们的肠胃,又把他们变成老皮厚脸的、沉迷精神会餐的饕餮。与此同时,伙食越来越坏。到后来,真正的粮食完全不见了,给我们吃的是“代食品 ”。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窝头,用的原料是乾白菜叶和一种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据说其中含有10%的淀粉。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养分,但是我们当中马上就出现了可怕的、鲜血淋漓的消化道问题。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员,由于长期便秘,差点儿因肠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应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们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长开动脑筋,请一位过去制造精密仪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这件精密仪器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贵食品分成均匀的份额,发给各人。在他运作的过程中,几十只眼睛都紧盯着他和他手里的秤杆,在运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开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变质的,谁分到谁倒霉。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几片实在无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们扔在门口一条大家夜间用作小便池的水沟里。一位难友、前共产党员,马上跳下去,把它们捡了起来。正当他把它们一片一片往嘴里塞,一名队长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说:“快扔掉!你不要脸!你还当过党员哩!” 他回答说:“但是我饿啊!饿啊!”他继续咬嚼,直到吃完为止。晚间政治学习,我和他都受到严厉批评,我的罪名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那位共产党员的罪名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饿啊!饿啊!”
其它一些饥饿难忍的难友开始搜索新的食品资源。有一位逮到一只田鼠,他趁队长不在眼前,捡到两块砖和一些乾树枝,点起火来把它烧熟,狼吞虎咽吃下肚。还有一位逮到一条蛇,他送到伙房去,让一个伙夫做成一锅蛇羹,两人饱餐了一顿。
我既无想象力又无本领去开发非正统的食品资源,在全中队是第一个严重浮肿病号。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肿,两腿软弱无力,下地劳改时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样子,因为周围没有镜子,但是从战友们枯槁的面容,我不难想象自己已经面目全非。不久之后,我上了严重浮肿病号名单,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义” 的食物补助。每天晚饭后,我去伙房领一个用旧报纸糊的口袋装的麦糠,和一碗猪骨汤,那是用农场养猪场饿死的小猪骨头做的。我成了难友们羡慕的幸运儿。可惜我的好运为时不长,因为小病猪和麦糠的供应都断绝了。越来越多的难友的浮肿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他们来不及分享我短暂的好运了 。
二
虽然党报和管教干部都避而不谈,即便在与外界隔绝的劳改农场,大家都知道全国正在经受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我们是从三分场场长的大报告中才领会到情况是如何严重的。他首先大谈“三面红旗”,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无比正确,又罗列统计数字证明它们的光辉成就。然后,他把近年来的饥荒完全归罪于气候反常、粮食歉收,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实行一项符合共产党一贯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措施。过去,给劳教分子寄递食品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食品包裹不利于思想改造。眼下,根据新的情况,准许家属和亲戚亲自递送食品,教养分子本人也可写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却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
我们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义”果实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妻子亲自送来的小麦面烙饼。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我们大家又饿又馋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这种不可思议的美味佳肴。我没有写信给怡楷传递“革命人道主义”的新信息。她远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让她为我的处境忧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饼,我不止是眼馋了。我想到怡楷家里人就在天津,离我不远,也许我可以向他们求援吧。求还是不求,这是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天的问题。有一个政治贱民作为近亲已经够他们受的,我还能让他们冒政治风险送食品包裹到监狱来吗?我能忍心让我那慈爱的岳母为我的处境忧心忡忡吗?这时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讲的话: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问题是“活下去还是不活”。面临生死攸关的挣扎,我抛弃了重重顾虑,向我那些好亲戚求救。
1961年元旦后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肿恶化没有出工,队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进屋子我就看见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旁边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员。四哥当初上的是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肃反运动中,他被诬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尽了身心摧残,以致精神崩溃。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们家,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后来还没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病还没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谢天谢地,他还可以不辞辛苦来探望他病重的妹丈。
接待员站在一边监视我们的行动。四哥打开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鸡蛋、一块煮羊肉、还有我岳母亲手为我做的十个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萝卜,接待员出面干涉了:“不许收咸菜。对浮肿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萝卜放回手提包,让我很失望。他告诉我这些食品都是从黑市用高价买的,但是,只要“ 革命人道主义”继续实行,他们就一定想方设法再给我送吃的。这时候接待员心不在焉向外面张望,我飞快地把手伸进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萝卜,塞进我的破棉袄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却胆小怕事,给我的胆大妄为吓呆了。
(31)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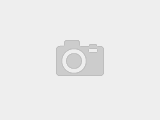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