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你真客气。把你的包也放在车上吧。”
老王急不可待地撕开盒子,津津有味地大嚼起饼干来。没多大功夫 ,他就把一盒饼干吃光了。他扔掉空盒子,咂着嘴说:“哎呀,这饼干真好吃!欢迎你再来用我的屋子,没问题,没问题 。”
到了值班室,我又来到那位值班员面前,准备他对我大发雷霆。反正豁出去了。
“干什么,李怡楷?”他吃惊地说,但并不是怒气冲冲的。“你说好不来的,怎么又来啦?我对你和你右派爱人这么宽大,你却不守信用。我们可以把你的表现报告你工作单位,你知道。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嗯 ?你很清楚我不会让你再见他的。”
“这是我们的女儿。”我指着坐在我腿上的一毛。“她是在她爸爸离家后出生的,今天是她三岁生日......”
“你带她来这么个地方过生日,第一次见她父亲,真有你的!小姑娘好漂亮!”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好吧,好吧,你是个心气很强的女同志,我拿你有什么法子呢?我知道我这人心太软,可是......得啦,等你爱人收工回来,你再见他一次吧。十五分钟,一分也不多,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你可答应?”
“我答应,我答应。他若身体好了,我也就安心了。他若好不了,我再来也没用处了,对吗?”
“我要书面保证。”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白纸。
我从他办公桌上拿起一枝钢笔就在纸上写下:
保证书
我保证不再来探视我爱人巫宁坤
李怡楷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
宁坤又一次看见我,同时第一次看到女儿,他那呆滞的双眼露出了喜色。我事前尽力向三岁的孩子作解说:爸爸因为有病还得下地干活,生产粮食给我们大家吃,身上穿着带泥巴的劳动服,样子会很难看。然而她还是被爸爸的样子吓坏了。我紧紧搂着她。提醒她我昨天和今天在路上跟她说过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就笑眯眯看着她父亲,羞答答地叫了一声 “爸爸!”
“这就是我的小公主!”宁坤笑逐颜开地说,但我听得出他的声音里含着眼泪。“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真是一只小凤凰!可惜咱们今天不能在咱家的宫殿里庆贺你的生日,小毛毛!”
“不要紧,爸爸。妈妈说你快回家来啦,明年咱们在我的宫殿里庆贺我的生日。”
“可是你的宫殿在哪儿,我的小公主?”
“在我故事书的森林里,当然嘍喽。你多傻,爸爸,连这都不知道!”宁坤和我都笑了起来。
“爸爸,我过生日,你不亲亲我吗?妈妈亲了。姥姥亲了。大伙儿都亲了。”
宁坤踌躇了。“我这身泥巴会弄脏你的嘴巴和漂亮衣服的。”
“别犯傻,爸爸!姥姥会给我弄干净的。来吧!”
宁坤把她搂在怀里,亲了又亲。
“你是个心气很强的小姑娘,跟你妈一样。我太高兴了!”他又朝着我说:“有一天,这只小凤凰会翱翔云霄,在天堂门口歌唱!”我们的十五分钟一转眼就过去了。配给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抗争。宁坤急匆匆赶往地里去劳动 ,他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我瞧见眼泪流下他那苍白的两颊。
第十章 暂回人间,1961 – 66
一
1961年6月29日,中午过后不久,我和几百名劳教、劳改犯一起在农场收割小麦。骄阳似火,汗如雨下。忽然,值日队长通知我去和一名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我心里有点打鼓:人事干部找你往往没好事。来人是一个中年男子,身穿短袖白衬衣和草绿色军裤,蹲在打谷场边上的树荫下。他用近乎正常的声音招呼我:
“巫宁坤吧?你生病了,对吗?现在怎么样?”
“好一些了,”我含糊地回答,还不知他的来意。
“那就好。农场领导决定让你回家,保外就医。革命人道主义 ,你明白吗?”他用官腔宣布。“你现在就回队部去,先把帐结了,然后收拾行李。明天一早,总场有大车送你,还有其他几名保外的,一起去火车站。明早八点整,你在分场大门口等着。人事科有人来发给你一张火车票。保外期间要好好表现,明白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什么话要说,只含糊地说了声“谢谢”。事情的变化来得突然,虽说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却也简单得不可思议。复杂的感受让我不知言从何起。“你回家,保外就医。” 那么简单,那么说一不二,正如当年不经审判一下就罚我无限期的劳教。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听任社会主义政治风云的摆布!自从那个四月十七我被押上囚车之日,三年多的黄金岁月被糟蹋了。我无日无夜不梦想释放回家。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亲人身边,可是又觉得前途茫茫。会思想的芦苇连思想也不会了。我疲惫不堪,连怨恨的力气也没有。我只想摆脱几个月来如影随身的死亡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同班的难友,爬上大车,从人事干部手里接过一张硬席火车票和保外的文书。我必须在天津换车,于是我下车后坐上一辆三轮车直奔幸福里岳母家。熟悉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似乎不真实。我真的是在生者当中吗?在胡同口,我撞见了怡揩的一个侄儿,四年前最后一次见面他才六岁。他没认出我,正如不久前一丁来探监时背给我听的那首唐诗里说的,“儿童相见不相识。”他一定给我的囚首垢面吓坏了,一认出我来就飞奔回家,用最大的嗓门儿喊道:“老姑父回来啦!老姑父!”我的岳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泪流满面,马上就去给我泡一杯热茶,老人家知道我爱喝茶。我告诉她我是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家,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怡楷的众位兄姐看到我的惨状都流泪了,但庆幸我活了下来,又放了出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说大家给我送去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救了我的命,想让老人家感到欣慰,反而又引她流泪。当时一毛住在大姨家,就在附近,三姨去领她回来。我女儿起初不认识我,过一会突然想了起来,一下扑到我怀里:“你是爸爸,妈妈带我去那个好怪的地方看你。噢,爸爸!我不让你再回那个可怕的地方去!”我答应她我决不回去,姥姥听着又流泪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给怡楷发了个简短的电报,告诉她我四号到家,然后就先搭火车去北京看望老母和妹妹。那天正好是“七一”、中共的四十大寿。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相形之下,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国的侏儒。我想起五年前我从观礼台上遥望他踌躇满志向广场上狂呼“万岁”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一座座新建的高楼正面悬挂着红彤彤的条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和公车上面有菜色的乘客、沿街食品店里空空如也的橱窗,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想起十年前初次来到这座古城新都时犹如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土的感受。现在我觉得更像一个从死亡归来的游魂,我口袋里的保外文书把我和首都的芸芸众生划清界限。这些好人会怎么想,若是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件?他们会不会,像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那个小城镇安分守己的居民看到新释放的犯人华尔让的黄护照时那样,吓得退避三舍?或者,他们会不会,像小说中那位慈祥的主教那样,为一个“危险的犯人” 提供食宿?幸好我不需要到一个小旅店去求宿,而受到老母和妹妹泪如雨下的接待。
(41)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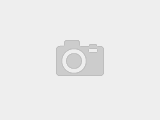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