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用家里唯一的一张椅子当“书桌”,坐在一张小木凳上,一面挥汗如雨,一面为两本读物编写详尽的注释。这时候,其他教师正在度暑假。我把两本注释送给杨教授审查批准,然后交打字室打印。九月初开学上课,第一次走进教室上英三的泛读课,面对二十几个男女青年学子,恍若隔世。顾不上猜测学生怎样看待这个戴着两顶“帽子”的老师,我把精神集中在讲课上面。所谓泛读,作为精读课的辅助性课程,一向不受老师和学生重视。首先,由于受从“老大哥”引进的教学法的影响,英语阅读课早已被简化为学习词汇和语法重点。精读课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一大堆分析语法结构用的专门名词。课文在这个过程中不见了,因此学生并不真的学会怎样读书。泛读课的要求更低,学生只要记几个新单词,会作简单的复述就行了。当年我说过,这种机械的方法是培养学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径。
现在既然在教育原则上没有发言权,我至少可以认真对待我自己的教学工作。我已经为学生准备了详尽的注释,没有必要再在课堂上花时间讲解生词和语法。想到我在劳改营里如何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的小说相依为命,我就有意探索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通过对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锐感应,培育独立思考,从而有助于一个自由心灵的成长。我朗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声泪俱下,使一个共产党的自由战士在一个共产党的劳改营囚徒身上再生。作为一个热爱学生又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契普斯的形象无形中使我的学生更亲近我,尽管政治辅导员一再警告他们不得与阶级敌人“亲如一家”。学生交来的作业中有时夹带一些表示钦慕的字条,情意那么感人,害得我这“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泪下。一个叫小张的男生聪明好学,他感谢我的“诠释和分析”为他“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新世界”。小徐总是沉默寡言,面无笑容,在信里说他非常同情我,因为他教中学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又说我的讲授“照亮”了他压抑的生活。我撕毁了这类字条,又警告他们千万不能再做这种鲁莽的事,否则我们都会在政治上“犯错误”。
同时,一经我班上的学生宣扬,其它班级的学生、青年教师、甚至合肥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有时候,来晚的人就得站在过道里,从开着的窗户听课。怡楷提醒我,“树大招风”。我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一方面,我得满足雇主的期望,他们给我这个宝贵的饭碗,仅仅因为他们相信我是个称职的英语教师。另一方面,我也得躲开同行间的妒忌和政治问题的激流险滩。处于这种情况,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也许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可是,天哪,如果我停止把语言作为人文学科讲授,我对这些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还有什么用处呢?得啦,不管怎样,我也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认识行事,尽管我已经如履薄冰了。
另一门是四年级的写作课,我每周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我们小屋里只有一张从安大租用的小书桌。这时一丁已经上小学,他每晚要做家庭作业,等他九点钟上床才轮到我用书桌。等我坐下开始看作文,我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为了提神,我开始抽起烟来,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杨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烟要贵五、六倍。有一天夜晚,怡楷和孩子们都已熟睡,一个点燃的烟头从我没知觉的手指间掉落铺在我脚下的、一块怡楷从天津家里带来的小地毯上。她给地毯冒出的烟呛醒,一骨碌跳下床,把我推醒,踩灭了刚烧起来的火。她果断地说:“马上上床睡觉。从今以后不许再开夜车,放烟火。”尽管这工作很辛苦,有时在学生的作业中碰到一个新鲜的想法或者说法,好像突然打开一扇窗户,可以看到一颗年青的心灵,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三
1962年9月我开始任教之后,外语系领导派了一名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青年英语教师小冯来跟我进修,同时监督我的思想改造。他在我指导下读英国文学作品,向我交读书报告,我每两周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不言而喻,我不断进步,但离“摘帽子”还有一段距离。小冯是一名复员的解放军尉官、共产党员,但天性谦和,笑容可掬。平常在看过我的思想汇报之后,他总会说几句鼓励的话。若是正好赶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他就会收起笑脸,批评两句“思想改造抓得不紧”。但是他来我屋里听我辅导,总是谦恭有礼,和孩子们有说有笑。每逢寒、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亲,他回校时从来不忘给孩子们带点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这些奢侈品是他们难得吃到的。我常纳闷,在这长达两年的微妙的双向交流中,他轮流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有过什么样的感受。我“摘帽子”的那天,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告解神父”的角色,也许会感到如释重负吧。
1964年7月4日,仿佛是纪念我保外就医回家三周年,外语系在大学七层主楼一间阶梯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员大会。一位人事处的干部在回顾我的右派罪行之后,宣读校党委决定,给我“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照事前的通知,我作了简短的发言,再次承认我的右派罪行,感谢党“给我一个新的政治生命”。我泣不成声,仿佛七年来积蓄的苦水冲破了防洪的闸门。有几个同事和我握手,祝贺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李主任答应我,很快就可以让我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同一天晚上,我们还来不及为我重新当上“人民”庆贺,怡楷就接到家里发来的急电:“母病危速归”。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六日抵津,才知道妈妈患肝癌,发现时已是晚期,经手术抢救无效,危在旦夕。老人家在医院病床上还惦着我这个老女婿,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讲给她听,这是她几年来一直盼望的。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亲娘,她又添枝加叶说我已恢复教授职位,享受原先的工资待遇。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一个悲痛欲绝的女儿还能给她垂危的母亲什么别的安慰呢?我怎能忘记她老人家给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如许的爱心和理解?我怎能忘记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监时转告老人家的话,“好人受难,耐心忍受”,一句话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她在7月8日逝世,正好是我们俩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我清清楚楚记得她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作为“婚宴”。她一辈子生活简朴,受苦受难,而从她自己所受的苦难中,她找到爱人的力量,尽力帮助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她完全无愧于她的受难 。
八月初怡楷奔丧归来,副系主任姚老师约她面谈。他通知她,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爱人已经摘了右派帽子。至于我本人恢复公职一事,拖到年底,李主任和人事处的交涉毫无结果 。外语系党总支一位委员向我宣布,临时工工资待遇加十元,还说:国家经济目前还有困难,这是党组织的“一点心意”,表示肯定我在思想改造和教学工作中取得的进步。事前我已听到,人事处长说得斩钉截铁:“一旦开除,永远开除。”这象征性的加薪意味着我们的伙食中可以增加一些鸡蛋,但是也让我直面我的“新政治生命”:我是一个“摘帽右派”,如此而已。帽子摘了,不错,但仍旧是“右派”,这是今
后许多年我无法逃避的政治现实。
(44)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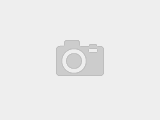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